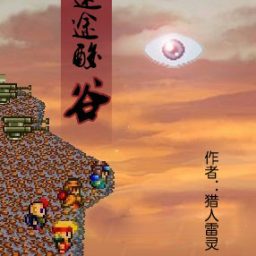《重装机兵之迷途酸谷》第十九章:蔓罗蒂之死
我愿提及那些心烦的事情,也不愿向别人提及。我不是时常摆出悲悯面孔的可怜虫,我也不愿活在姐姐的光环下。可我又不得不依靠姐姐的人脉,这样的现实,我难以接受。
我问那个男人猎人办事处的所在,他告诉我,猎人办事处就在这栋房子里。他还告诉我,他有名字,他叫蓝尧。
蓝尧?好吧,可我无论如何得去领赏金了。我默默地想着,厄尔尼诺这个鬼地方让我头昏脑胀,我原本打算先领赏金,打听霞大姐的消息,还要给尼鲁大爷写信,可 是这些事情全被我忘记了。这一路的邂逅与意外令人应接不暇,究竟该从哪件事做起,或许我需要一支铅笔把他们写下来,可我连买一支铅笔的钱也没有——我竟然 把领赏金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。
在那片寂之荒野里,我吃着不咸不淡的食糜罐头,半饥半饱,不至于饿死。在那张狭不能翻身的床上,我一次又一次从梦中冻醒,却又能昏昏然再次入睡,然后再次 被冻醒,再次入睡。我喝的是冰凉的水,这能使人清醒,我也会带着水桶到战车外面洗脸,有时是早晨,有时是晚上,但凡我醒来就会做这件事。我一次又一次地大 意,那些能发射光束的眼睛、能发射炮弹的身体不知躲藏在哪个角落,掠夺者也是无处不在,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我会死掉,可是,死了又能怎样呢,我想着,倘若我 死了,这世上还有多少我惦念的事,有多少人会惦念我?我想来想去,总觉得我的死就像一粒沙尘随风而逝,消失得无影无踪,化作一片长久的沉寂。
不过这个世界从不缺少死亡,那么姑且活着,至少还有恒多事情等我去做。
因为我始终没有吃饭,饥饿感把我从遐想中拉了回来。我想起赏金的事情,于是我开始在大厅里四处寻觅。这里左面是道具店,右面是休息室,中间有一扇门,我猜那就是猎人办事处,我过去推门,没有推开,门被锁着。
“这里面就是猎人办事处?”我指着门问蓝尧,“为什么锁着门?”
“自从厄尔尼诺沦陷,里面的人就走了。”
“他们什么时候回来?”
“很难说……”他犹豫了一下,“其实,猎人办事处里都是我们的人,自从掠夺者攻下厄尔尼诺,我们接到上面的指令,暂时关闭这里的猎人办事处。”
“这指令是谁发来的?”
“猎人办事处的总部。”
“哦?”
我疑惑着,蓝尧见我不说话,问我:
“有什么问题么?”
“那个总部又是一个什么组织?”我问他,“我只是觉得有些奇怪……”
“有什么奇怪的,谁不怕掠夺者?不过猎人总部是什么,我也不知道,关于总部的情报貌似很稀少。”
我靠在门上,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
“赏金,我的赏金怎么办!”
“你要领赏金?这容易,我把他们叫来给你派发赏金,总部那里就叫他们搪塞一下。”
“这样不好吧……”我说。
“没什么,你是玛丽亚的弟弟,那就是我们的人。”
“可我不想加入什么组织,我只是受沙漠之虎的指引来见金牙的。”
“你是说沙漠之虎?那个极度自负的家伙么?”
我苦笑了一下,什么也没说。
“我先去找金牙,但愿你在晚上就能见到她,猎人办事处的人我也会帮你叫来。”他说着,“你留在这里,如果有人问你是谁,你就说你是我新招的杂工。不要在乱走,如你所见,厄尔尼诺不是一个太平的地方。如果你非要去看那对姐弟,我劝你还是小心一些,他们是惹了大麻烦的人。“
我默许了他的话。
那个好心的地下党走后,我在屋子里坐了一会儿。我最终还是出去了,拿着那个热水袋和毛绒垫子。
下午的阳光散射着,天空昏黄发白,似乎被迷雾笼罩着。气温似乎更低了,这也许是风的缘故,把阳光的温暖吹散,留下一些锋利的小刀子,乘着寒风,扎在人的手背和脸颊上一阵生疼,我这才想起——我把手套和坦克帽落在自己的战车上了。
战车里的确暖和得多,不过我可不想躲在里面。也许我离开这个小空间太久了,除了暖气,我还闻到了一股腐尸的味道,车厢已经很久没通风了,可是我不能打开车 门,因为我没有暖风机,不能让积攒下来的热气流走,我还不想在夜里挨冻。我拿起帽子和手套,临走前想起013猎人说过的关于“身份的证明”,于是我把bs 控制器取了下来。
就要与金牙相见了,真不知道会他是一个怎样的人,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告诉我过去的事情。自从离开了阿梓莎,我感觉自己好像置身迷雾中一般,我邂逅了那么多 人,他们的出现仿佛是命运的安排,为我驱散一片又一片迷雾,脚下的路得以越走越远,又似乎是别无选择。可我能感知到,我正踏入一片别人从未涉足的区域,这 里面一定隐藏了什么。
寒风呼啸,总觉得这两天的天气异常的冷。
牢笼旁的姐姐搂着她的弟弟,纹丝未动。她刚才穿着一件大衣,那件大衣现在已经披在她弟弟身上了,她自己只说穿着一件肥大的毛衫。当我走近她时,我才发现她的肩骨很明显地凸出来,像柱子一般撑起毛衫。
“她一定是冻僵了!”我想这,“但凡如此,不会已经死了吧!”我又疑惑起来,为什么只有她一个人守着这男孩?他又是因为什么事情被关进监狱?她还扑在他的 身上,中间隔着一层铁栅栏,我站在她背后,望着她出了神。不知过了多久她的手微微颤了一下,她醒了,缓缓地把自己的胳膊从男孩身上缩了回来,我惊了一下, 不知她要干什么。她缓慢地抬起手,摸着正在随风飘扬的头发,把它们向一起聚拢。她从裤兜里拿出一截小绳捆头发,她很卖力地打结,似乎用了很多体能,等她做 完这一切之后,她忽然瘫倒在地上,头发又重新散开了。我立刻蹲下去叫她,把她扶了起来。
太阳躲进云层,大地披上了一层阴影,此时的风变得更弱了,声音像一支残破的长笛。
她缓缓地睁开眼,眼睛里布满血丝,我看她的脸冻得发白,眼睛又红又肿,却不见眼泪。此时她与我对视,我看到她的脸生硬地笑了笑,似乎只是微微地动了一下。
“你……是……”她神情恍惚,似乎用全部的力量来说这句话,然而我听到的只有气息声。
我把脸凑近一些,告诉她我是道具店新来的帮手。听了我的话,她僵硬地笑了起来。
我把暖水袋放在她的怀里,她抱住它,缓缓地低下头,把脸凑到热水袋上。
“里面的人是你的弟弟么?”
“是……”她发出那种可怕的气息声,差点淹没在风中。
“他是个技工?”
我问她,却没听到她的回答,她只是一动不动地坐着,风声喜怒无常,似乎她的声音已经完全被遮蔽了。
忽然间她抬起头,望着我手里的垫子,她的嘴角微微动了起来,我把头凑过去听她说什么。
“能……不能……把它给……埃吉鲁……”
她是让我把垫子放到牢笼里那个人的身下,我立即把它塞进笼子里,把他们平整地铺散开,然后把那个男孩拖到了垫子上,那个男孩应该叫埃吉鲁,我刚才似乎听到了这个发音。我把披在埃吉鲁身上的大衣重新盖好,那是一件破旧的棉大衣,不过还有些暖气。
她伸出手,拿着暖水袋,她似乎在寻找我,我明白了她的意思,把暖水袋塞到埃吉鲁的衣服里。
我觉得还不够,把自己的皮手套让给了他,这下他已然是全副武装了,我还想把坦克帽让给他,只是那铁栅栏太密集了,坦克帽塞不进去。
我想到了那个女人被风吹走的帽子,于是顺着风向去寻,终于在不远处的一个角落找到了它。当我回来时,那个女人又瘫倒在地上了,腰前的两块骨头把毛衣撑起。里面的埃吉鲁也晕着。
我搀着那个女人回了道具店,好在路途并不遥远。不过当我摸到她的皮包骨头,心中不禁一惊。回到休息处,我把她放在长椅上,给她喂了点热水,又把一块热毛巾敷在她的额头上,希望她早些醒来。
不知过了多久,我又听到了那个只剩下气息的声音。
“猎人……埃吉鲁怎样了?”
“他——还好。”我也不知应该如何应答她。
“我现在眼前很黑……什么也看不见……我可能就要死了……”
我看着她,她望着天花板,目光一片空虚。我心想她怎么说这种的话呢,一个人怎么能这么轻易地死去?我不知该说什么好,想安慰她,又无从开口。
“如果……我死了……埃吉鲁……怎么办……”她的声音发颤了,“……他没死……我先死了……如果……活下来……一定会恨我……扔下他……”
“你不会死的……还是再喝点水吧。”我想她的脑子一定是冻昏了,不然不会说这些胡话。我想喂她一些热水,让她继续睡一会儿,她却把头转开了。
“猎人……能不能……求你一件事……”
“你怎么知道我是猎人?”我问她。
“气味……骗不了我的……而且……你怎么可能是这里的帮手?……别瞒了……我知道……跟这里……的人……都是大有来历的……”她的语速微微加快了。
“呵……”我摇摇头,轻叹一声。
“猎人……埃吉鲁……我的弟弟……他没有错……他没有母亲……一直受苦……好不容易成人……我想让他活下去……”
我坐在她身边,用勺搅着水,一面听她说话,心里突然一阵酸楚。
“猎人……在听……听么?”
她用一种近乎绝望的语调呼唤我,她的气息声越来越可怕,就要断气似的。我想也许事情比我想得严重一些,我不禁“嗯”了一声回应她,把被子放在地上,听她说话。
“我……要死了……可……如果……救救……救埃……”
她的手颤抖着抬了起来,像一支枯枝。我立刻伸手抓住她,我希望她能安静点,可我似乎抓住了一个冰块,她的手冰得吓人。
她终于安静了,不过只有一会儿,她的嘴又开始动了。我只得把耳朵凑近她的嘴,听她说什么。
“猎人……你也有……也有……亲人……你……”
“没有。”我打断她的话,抬起头,“我没有亲人,一直孤零零地活在这个世上。”
她的气息声忽然变得混乱了,我有些后悔自己向她发情绪,我看了看她,她的嘴唇毫无血色,面色苍白,比雪还要纯洁。
“麻烦……去看……看……埃……埃……”
她不再说话了。
我本打算给她弄一些热食物,可是她让我去看她的弟弟,看她那么虚弱,我也只好默默地服从了。现在她的样子很平静、很安宁,她一定是睡着了,我也觉得自己不好再打搅她了。所以我悄悄地走出了道具店。
在厄尔尼诺的这两天格外漫长,就直觉而言,我越来越觉得不安,就像当初在霞大姐那里的时候。
我感到异常寒冷,才发觉自己的衣服过于单薄。我把手伸进兜里,却摸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,我很好奇,掏出来以后才发现那是伊丽特送我的手帕。至于手帕为什 么硬邦邦的,是因为上面还沾着我的血渍,记得前些日子我还用它处理过一处烧伤伤口,事后我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。我突然愧疚起来。
倘若我是一个强者,我自然应该承担一切。可我本应该找个地方住下,安安分分地等猎人办事处开门,领赏金,然后离开这里继续做猎人,似乎连救人那种事情都不应该去招惹。
至于那个女人——那个女人叫什么?我似乎还没问过她的名字,只知道他的弟弟叫埃吉鲁,等我回去再问。如果蓝尧回来,也许我能为她争取一些同情,看她现在的样子实在是可怜。
任何事都不会在我的意料之中,那便走一步算一步,不去胡思乱想。风声在我的耳边呼啸着,遮蔽了很多声音,我裹了裹衣服继续走。
太阳渐西,很多东西都看不明朗了,囚笼那边似乎有人站在里面,我很平静地向那边走,刚刚看清里面的人就是埃吉鲁时,就听到他在冲我喊:
“喂——喂——”他有些怨愤。
我抱紧身子一路小跑到他面前,他握着铁栅栏,眼巴巴地望着我。我又瞥了瞥他的周围,垫子散乱地铺在地上,同时被遗弃的还有暖水袋水袋,只有那间衣服被披在她身上。
“你看到一个又高又瘦的女人了吗?”他用一种责难的口气问我。
“看到了。”
我把她姐姐昏死,以及后面的事情都给他讲了,我讲的不紧不慢,那家伙却越听越紧张,他那张细长的脸上露出紧张的情绪,我见他的反应过于强烈,于是隐去了一些情节,只说她的姐姐已经醒过来了,吃了东西,现在面色红润得很呢。
“一会儿我再去弄些暖和的吃食,她也会给你带来一些。”
“可是她很久以前就吃不下东西了。”
“什么?”
“我也不清楚,虽然她从没有承认过,可她总是病泱泱的,越来越瘦,一定是得了什么病。”
“你知道她得了什么病?”
“她从来都不告诉我这些事情,我也不敢问她。”他嘟囔起来。我发觉事情似乎很严重。
“她这个样子多久了?”
“很久了。起初她说她把酒吧的工作辞了,要在监狱外面等我出来,要么陪我一起死。她在外面昏过去好多次,后来越来越频繁,最近她连话都不说了,可我也不敢问她究竟怎么了。”
“你姐姐她叫什么?”
“蔓罗蒂。”
我告诉他千万要老老实实地呆着,然后风一样地跑回道具店。迎面正是太阳落山的方向,那面的天空一片瘀青,还有些许血紫的瘢痕,那个太阳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,远处投射出恍恍惚惚的黑影。我只是后悔,自己怎么如此大意,蔓罗蒂很可能已经死了。
路上我责备自己太大意,但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变得如此麻木,竟然连一个人的死都看不出来。
回到道具店,是蓝尧开的门,我看他一脸沉重的样子,急忙问他:
“那个蔓罗蒂怎么样了?”
他不理我,只是甩头走了。我没心思管他,急忙跑到放蔓罗蒂的那个长椅前,蔓罗蒂还是刚才的样子,只是满脸苍白,我伸出手去摸了摸她,没有温度,我又把手指凑近她的鼻孔,没有呼吸。我的脑间瞬间闪过一个念头“死了?”
“她已经死了!这人是你拉回来的吧。”蓝尧在一边坐着,拿出一支烟点上了。
“我背她回来的时候她还没死!”我不由自主地辩解着。
我还在为蔓罗蒂的死感到不知所措,门外却有两个人正在走过来。其中一个是卡奇娅,我是认识她的,可是另一个我并不认识,那是个女的,穿着同卡奇娅一样的衣 服,不戴风帽,一头棕色的短发露在外面,其实更像一个男人,她的眼睛很大,很有神,不过她的眼神流露的信息很少,只有冷峻。
她不知在跟卡奇娅说着什么,走进了屋子,看到屋里面有一个似乎已经死去的人,还有我这个陌生的面孔时,她停住了脚步,呆在门口,卡奇娅也是如此,而且又惊讶又惊惶。
那个女人瞅了蔓罗蒂尸体一眼,瞅了我一眼,又去瞅蓝尧,问他:
“这是怎么回事?”
我看了看蓝尧,他一脸木然,一直在吸烟,他这时候把烟头扔在地上,抬起头冲卡奇娅喊:
“快把门关上!”
卡奇娅这才像从梦中醒来似的,很慌张地把大门关上了。
那个女人走到了蔓罗蒂身前,看了她一会儿,也把手指凑到她的鼻孔处,她问:
“这是酒吧的蔓罗蒂?她死了?”
“死了!”蓝尧说。
“怎么死在这儿?”
“问他。”蓝尧冲着我说。那个女人的目光立刻转到我身上,她那双眼睛盯得我难受,我知道这次一定又是我惹出事端了,而且也躲不掉了。
“是我把她弄回来的。我需要技工做伙伴,听说监牢里面关的就是个技工,过去看了看,她就坐在监牢外面,已经晕过去了,所以我把她带了回来,谁知道她这么快就死了。”我也装出一副又气又恨的样子来。
“她是怎么死的?”那个女人低着头,按着蔓罗蒂手上的皮肤,口气很平静地问我。
“我不知道。她死的时候我并不在场,我也是刚回来。”
那个女人又盯着蓝尧,蓝尧抬起头看了她一眼,说:
“你别看我,我什么都不知道,我也是刚回来。我很早就跟他交代过,别去招惹那对姐弟。”
“真是灾星!”蓝尧恶狠狠地说完这句话,也就不再说话了。他又掏出一支烟,低着头吸了起来。
这时候卡奇娅凑到我身边,她把嘴贴近我的耳朵说:
“你怎么能惹出这些事来。”
“我没有!”我小声回复她。
“看到她了么,她就是金牙,本来我与她刚才商量,让你去找银牙,那是个撬锁高手,一定能把那个技工神不知鬼不觉地就出来。可你怎么这样沉不住气,现在弄得蔓罗蒂还死掉了。”
她的意思是我弄死了蔓罗蒂。我向她解释,蔓罗蒂的死真的与我无关,可是她却说即使无关也脱不了干系。
金牙女士还站在蔓罗蒂前,此时她似乎要走了。
“她的喉部很大,看样子是得了什么病,怪不得她那个爹爹把她赶出了家门。”金牙说,带着一种嘲讽的口气。
“那个人酗酒,不过心肠不坏。”卡奇娅说着,“接下来该怎么办?”
“谁惹下的货,谁去解决呗。明天必须把这尸体处理掉。”
我突然想到了还被关在囚笼里的埃吉鲁,于是插了一句:
“那个技工怎么办?”
我是问那个金牙女士的,此时她正在往道具店里屋走,听到我的话,忽然停了下来,转过头来看着我。
“你问我怎么办?你说应该怎么办?”她用嘲讽的口气反问我,并且瞪了我一眼。然后她推开道具店里的一个油桶,里面有一条地道,她钻了进去。
这下子屋里变安静了,似乎一直很安静,只是我自己没注意到。蓝尧还在一旁吸烟,他已经一连吸了两支了。卡奇娅走到蔓罗蒂的尸体前,看了看她瘦得如竹条一般的腿,叹了口气,把她已经耷拉在凳子下面的头发拢在一起,放在她的脑边,让她的遗容看起来安详一些。
“这个女人怎么看都是一副冤相!”卡奇娅说着,“喂,蓝尧,你知道这个女人的事嘛!”“不知道。”
“我听酒吧那边的朋友说,她哑了,还不能吃饭,整天病泱泱的,后来被解雇了。”
蓝尧坐着,深深地吐了一口烟,说:
“跟我有什么关系。”
“没什么,世道变,人也变,只是心里不平。”
“你有什么不平的,这种时候谁不是保自己。”蓝尧说着,似乎想起了什么,开始自言自语起来“保自己……”
“卡奇娅,你过来,靠近一点。”他叫着卡奇娅,然后小声地问她,“你知道你领来的那个猎人谁么?”
“不死女战神玛丽亚的弟弟,我早就知道了。”
“那你把这件事情告诉金牙了?”
“当然告诉了。”
“金牙什么反应?”
“没什么反应,她的脸上从来不挂事情,你又不是不知道。”
“你们都是女人嘛,这种事情怎么不好猜?”蓝尧说着,把烟丢在地上,随意踩了几脚。
“倘若说——”蓝尧突然间有了兴致,“有一天我也被掠夺者干掉了,你会怎么样?”
“什么怎么样……”
“比如吃不下饭,睡不着觉,终日以泪洗面。”
“我才不会呢,我该吃就吃,该睡就睡,为什么要哭,为了你这死鬼?”
“我想,什么时候你们这两个没心没肺的女人能抱在一起哭成一团,我跟绯也算死的瞑目了。”
“去你的,就算我那样,金牙也不可能那样。”
这会儿两个人开始拧在一起打情骂俏了,我就坐在一边,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多余。
不过我也在开始盘算着自己的事情,卡奇娅说金牙让我去找一个叫银牙的人,那我就去吧,如果他能从掠夺者眼皮底下救出埃吉鲁,那是最好,如果救不出也无所 谓,我现在有了赏金,哪里都可以去了,不如找个安身的场所等到春天,春天里怪物就多了,就可以狩猎了。而且我也是这时才想起一件事,蓝尧答应我打开猎人办 事处的门,他还没做呢。
我正胡思乱想的时候,突然发现这屋子里就剩下了蓝尧一个人,卡奇娅不知去了哪里。我问蓝尧,他说她去秘道里找金牙了。这时候他也想起了白天他答应过我的事 情,于是帮我打开了猎人办事处的大门。那里面的布置跟马多差不多,堆满了一些不知名的机器,还有一张床。蓝尧把我的ID卡要了过去,在一旁操作着机器,我 就在那张床上歇着,后来有些睡眼迷离的,索性躺在了上面。
过了很久,蓝尧才把我的赏金提出来,可我很困,已经没心思想赏金的事了。又是心里憔悴的一天,我一向难应付这些乱情。蓝尧说,让我在屋里面睡,明天就得离开这里去找银牙。我似乎默许他了,就睡死过去,后面发生的事情我也不记得了。
本文由管理员发布于:2018年01月15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