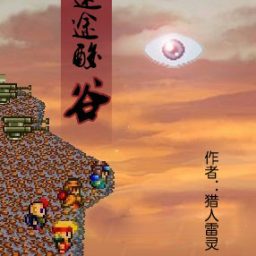《重装机兵之迷途酸谷》第十二章:锈蚀郊野
出了马多,我开着战车一直向东走。
这条路线本是计划好了的,但究竟要走多远,走多深,走多久,那可无从而知了。我只是徒然地驾驶着战车奔驰在这荒野上,虽然我知道我已经离马多很远了,可是我的眼前依旧只是一片一片的荒原,而不是沙漠。
但我哪里是因为没找到沙漠而焦急,我不过是因为找不到赏金怪物罢了,可是这种事情是不能心急的,我知道路越走越长,我也坚信的赏金怪物们一定会出现,事情总是会出现转机,只在于我是否能坚持到那个时候。
离别的苦痛已经淡去了很多,既然自己执意要走,就没有什么好后悔的。我已经成为了一名猎人,拥有了最强有力的武器——强大的战车成为了庇护我的躯壳,让我 有能力与赏金怪物们战斗。可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,我总觉得从坐进战车的那一刻起,我便失去了自由,好似被一个囚禁自由的牢笼。紧闭的车门,如同结界一般 把我与外面的世界隔开,我把持着方向盘,看着监视器里战车扬起的沙尘,迷茫、迷蒙、像梦一般远去——那些不能忘却的过往,都在飞逝着,我却没有机会抓住它 们。我又想起了阿梓莎的平凡生活。
我知道本不应该想太多,因为现在还有更棘手的问题等待着解决,那便是这辆战车。战车这个新奇的玩意我还从未接触过,虽然我的确会驾驶车辆,那是在阿梓莎的时候学的,只是最普通的车,所以我对c装备这东西一无所知。
在这片寂之荒野奔驰了许久之后,我停了一会儿,颠簸与杂音搅得我心神不宁,这下终于安静了些。我读了读《猎人手册》,之后大概明白了c装备究竟是个什么东西。
简而言之,c装备就是战车的控制系统,供给、监视器、雷达等那些数据都在这里,我可以调整他们,完成日常行进的操作,也可以与敌人作战。我的这个c装备有 四块显示屏、一个监视器和一个操纵板,通过显示屏可以看战车四面的状况,监视器上显示着有关于战车情况的数据,操作板是操作命令的地方,也是下达攻击指令 的地方。
至于《猎人手册》其他可看的内容——有对于武器的介绍,主炮是主要火力,威力大,资源少,我的只有16发;副炮包括机枪和一些放电枪、激光炮之类的东西,总之是威力小,资源多,而且资源都很便宜。
扔下这些,让我来看一看加西亚号的内部,战车里面并不算复杂,可用的东西也只有c装备,另加一个车座。c装备只是一些监视屏、操纵面板那样的东西,附在前 部的车壁上,好在没有占去太多的空间,四块监视屏嵌在靠左的位置,监视器在中间,下面是操纵面板,再下面的就是方向盘了。方向盘很小,而且还不是圆形的, 它的上下都有圆凹形的豁口,整个方向盘的样子好像一张被咬了两口的小饼,左右就凸了出来,方便驾驶者把持。
如此说来,车里面的确“不复杂”。可是,由于车子的空间十分狭小,就算是没有太多的设备也很窄。车座都是勉强被容下的,只要坐在上面双腿就会被卡在车座与 c装备之间的缝里面,油门与刹车那里的活动空间倒是很大,小腿可以自由活动,然而大腿却是动弹不得,想站起来更是不可能了。好在车座比较软,坐上去还算舒 服。
剩下的空间,就是我右手边的胳膊宽的一小块空地,这里主要是用来放小什物,比如《猎人手册》和水桶,不过也只能放一下一个。车坐后面的空间倒是很大,但那是为晚上睡觉的时候准备的,因为车座靠背的倾斜度可以调整,可以完全放平,这样就可以躺在上面睡觉了。
我又看了会儿《猎人手册》,感觉无趣,于是翻起c装备的菜单,想找一些新鲜的东西。BS控制器已经跟c装备连接在一起了,这是尼鲁大爷的杰作,当初他把 BS控制器给要去,就是想把卫星地图连接到C装备上,监视器的屏幕要比BS控制器的屏幕大很多,看地图更加方便。从监视器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所在的方位 ——我的确在往东走,但究竟走了多远却不能够测量,因为我还没找到什么标志性的参照物。
不过bs控制器仍然可以取下来。
还有雷达,对于它《猎人手册》也有记录,我只看了一点点。按照手册上的说法,当其他的存档机接近时,雷达上就会有显示,如果接近的是赏金怪物雷达就会“哒哒哒”地叫起来,若是赏金首还会有警笛声。我很好奇其中的原理究竟是怎样,可惜这些《猎人手册》上并没有记录。
其实,以上的这些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,直到现在我并没有遇到真正的赏金怪物,所以并不能证实什么东西。我想我还是收起《猎人手册》,继续赶我的路。
中午的时候,肚子有些饿了,于是便停下战车,到后备箱取了一瓶罐头。我拿到罐头后,我并没有直接回战车,而是靠着车门下面的车轮坐了下来,也许是在车里面 闷得太久了,我突然觉得这荒原上透凉的空气有一种微微的幽香。我一边吃罐头,一边抬眼远望,想要找寻一些值得我观察的景色,哪怕是一片枯黄的蒿草或是几棵 树的尸体。然而我竟没有见到丝毫,只有荒漠和滚动着的沙暴。
毕竟这里本就应该荒凉一些,连尸体都没有,更不要谈生命了。
远处的山隐藏在茫茫的雾霭之后,让人看不清它们真正的样子,那些雾气不断升腾,那些朦朦胧胧的山峰也跟着动了起来,我看得入了迷。记得马多镇是酸谷西南角 落里的一个镇子,可以说是最偏僻的地方了,它的北面和东面都是荒漠,西面和南面如我所见,满眼望不尽的山峰。我呆呆地望着它们,在想,山峰的后面究竟是哪 里呢?我依旧好奇地猜测着,虽然我早已知道那个不争的事实。据说很多人都去探索过酸谷以外的世界,可是山峰实在陡峭,不能开车,那些人便备足了干粮,踌躇 满志地徒步探寻外面的世界,然而直到今日也没能收到那些人的任何回音,他们全都一去不返生死未卜了。
可是,我想这一切与我的关系并不大。我呆呆地仰望天空,这天空好像大地一样,太阳遮着云翳的面纱,漫天折射着虚白的阳光,混混沌沌、沉沉闷闷,一幅没精打采的模样。风不断地钻进我的单衣里,似乎是想分享一些我身上的热量。而我,只能看着、想着,燃烧着我的想象力来取暖了。
后来,寒冷实在是不堪忍受,我不得不钻躲进战车里。在车门关上的一瞬间,我仿佛又与什么隔开了似的,一种失落感突然涌上心来。我当然明白这样一个道理,监 视器里看到的和自己亲手触摸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,即使我可以凭靠着监视器眼观四路,见到的也不过是一些虚像。然而我的准备又太不充足了,在这寒冷的冬 季里,我竟然没有带棉衣,只好老老实实地呆在战车里,只是这种孤独太难消受了。
路终究还是要走的,于是我发动引擎,继续赶路。
下午时,我到后备箱取了些水,又取了一些罐头,这种像药汤一样难吃的东西倒是很充饥,几瓶就足够我吃上几天了。这主要是因为天气渐冷,我要尽量减少打开车门的次数。
谈起这种便宜的罐头,我又想到了一些往事,记得当初我跟姐姐出来的时候,曾经搭乘过一段出租战车,那时吃的就是这种东西,吃过之后吐了一路——那时我并不习惯这种既不甜又不咸的味道,那时的胃也是娇惯得很呐,好在现在早已经适应了。
荒漠上突然刮起风来,这次似乎是更大的风,漫天都是被风吹起来的沙粒,像是一大群黄蜂呼啸而过。沙暴弄得我睁不开眼睛,我一边挡住脸,防止脸部被大沙粒伤到,一边暗自庆幸着:“若是我刚才吃了罐头,那我一定是满嘴的沙子。”
这种狂风的到来无非是在示意“要变天了”,而且四面确实变暗了,沉闷的雾霭早已退去,乌云压低了很多,而且都在飞快地移动着,灰色的乌云颜色深浅不一,时 而相互重叠,时而露出灰白的亮斑,但很快又被别的云层所覆盖。逐渐地天似乎更暗了,风也一直没停,自己的眼睛又忽然被风沙给迷住了,所以只得低下头来揉一 揉。
“真是可怕的天气!”
我一般揉着眼睛一边想,若是自己还有一个列车房就好了,记得小时候我总是习惯躲在屋子里,一旦变天我就一头扎进被子里,之后无论是刮风还是打雷,甚至是更 暗更恶劣的天气,也便与我无关了。然而,我现在只有一个人,无论是自然给予我的恩惠还是那些数不尽的风暴,我都要自己去选择,再没有人为我遮风,也再没有 人向我传授经验,我突然间觉得那样的力不从心,没有信心去面对命运赋予给我的东西,我充满了恐惧,完全是一种畏惧。
“暴风雨到来的时候,也许还会有雷暴……”
我想着。即使是掠夺者也需要自然之中的能源,这个世界谁都可以自以为是,但是终有那么一天一切都会荡然无存,如果真的存在那么一天,人类与掠夺者的战争又 有什么意义呢?一切终究都会走向毁灭,只不过或早或晚。可是自然不愿轻易去打破它创造的平衡,所以它才会姑息这场战争吧,但我觉得它是在作孽,难道无为的 意义就是容忍这场不义的战争继续进行下去么,自然的思想有时真是难以理解。
“谁才能阻止这场**呢?”
我想着。我最终躲到战车面里去了,因为我觉得实在没必要一边吃着风沙,一边想这种晦奥的问题。
自己没找到赏金怪物,还得受着这鬼天气的气,一想到这些我的心里真是别扭得很。风沙越来越大,监视器里只有混沌一片,根本看不清路,在这种情况下赶路会遇到各种各样预料不到的意外,我又只好不情愿地停下战车。
时间已经不早了,可这风沙没有丝毫停止的意思,我在战车里呆呆地坐了很久了,也有些疲惫了,便关上了灯,决定睡觉。我放平了车座的靠背,仰面躺在上面,脑袋枕着自己的大衣。
这是自己第一次独自在战车里睡觉,落寞的感觉不免让心酸,本想翻个身,因为那样会更舒服一些,却因为空间的狭窄而作罢。
接下来的几天,我一直在重复着这种生活,吃着无味的罐头,喝着带冰渣的水,整日朝着未知的东方驶去,困了便睡觉,睡好了就继续赶路,浑浑噩噩地度日。监视 器里的景色倒是变了一些,变得更荒芜了,地上的土粒越来越少,沙子越来越多,有时候一眼望去,只有这灰黄色的大毯子向远方延伸着,荒凉、突兀,再也看不到 它物,就连风中都夹满了黄沙,有时甚至会钻到你的鼻孔里。
前两天倒是飘了点儿雪,然而我还没来得及认真欣赏,那些雪就被风打扫得干干净净了。这两天天气又是异常的冷,尼鲁大爷的那件大衣也成了摆设,已经起不到御 寒的作用了。我又只穿了一些秋装——玛丽亚送我的那套,即使我穿上所有的衣服,我也必须尽量减少外出的次数,好让战车里暖和一些。我没日没夜地猫在战车 里,真好像在冬眠。但是,战车里面的确温暖,这车子虽没有取暖设备,但我发现战车内部的墙壁,也就是隔板,它的里面是空的,保温效果非常好,这还是我不经 意间发现的。
虽然我很少出去,但并不代表我不喜欢雪。我爱雪,从小就偏爱下雪的天,因为阿梓莎也是一块贫瘠的沙地,虽然有四季之分,却看任何四季留下的痕迹,除了黄沙 一年到头看不到丝毫的绿色。然而只有雪是例外的,只有在雪天之中,阿梓莎才能换一换颜色,那时候我也总是满心欢喜地跑到外面,去欣赏那个银装素裹的世界, 惊叹这这世界上还有如此美妙、如此纯洁的东西,后来每次下雪我都会去看。
当然,这次我也出去看雪了。但是这次的经历一点都不愉快,因为我遇到了赏金怪物,而且还差点丢了命——说起那段经历真叫人终身难忘。直到现在,回想起来仍然后怕。
记得那天夜里一直在下雪,清晨雪停了,我便驾车赶路。我一边开车前行,一边从监视器看着外面雪原,除了白茫茫的一片,什么都分辨不出来。从监视器里的景色 都是失真的,这种经验我早就有了,既然有了经验,我也就不甘于看这些虚景,于是穿上所有的衣服,披上大衣,扣紧帽子,撸紧手套,决定亲自到外面看。
这片寂静的荒野,荒漠不再是主色调了,大地披上了一层薄薄地白沙,突兀的黄色此时被柔和了许多,像是往上面撒了一把的盐,又好像是撒了一地珍珠磨成的粉, 它们纯洁、高尚,又很肃穆,决不同于它们覆盖之下的土地。风依然很大,白雪和着风飘飘洒洒,地飞来飞去,时而旋转,时而飘移,像是一群孩子,欢喜地喧闹着 就是不肯下落。
这种天气,平常的人自是不会被打扰。你看那混沌的天,似白似灰,比起它所创造的雪还要暗淡许多。然而对于一些漂泊的人,他们的感觉就仿佛天的颜色,忧郁的 颜色,这些人总会触景生情,一旦想起美好的往昔,便陷入沉重的回忆里。可是对于我,我丝毫不属于这两种人,因为此时的自己依旧高兴地欣赏着雪景,就好像小 时候那般欢愉。我想,唯有孤独的心才能容得下这么平静的景色吧。
随后,我跟着风跑了起来。风把雪吹到哪儿,我就跟到哪儿,好像中了魔似的。但在途中,我看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被风拖着,最后就落到了我的不远处。我有些好奇,于是就凑了过去,想要弄明白那究竟是个什么东西。可是在我还没到走到它跟前时,我就已然分辨出那是一只鸟。
“如果那真是一只鸟,倒是可以抓住它,好来打发一下旅途上的寂寞。”我天真地想着,丝毫没注意到危险的临近。在这种万物衰颓的季节里,就连赏金怪物都躲藏起来,荒原上又怎么会有鸟呢?
我终于走到那只鸟的身边,我便俯下身子去看那个小家伙,这时一阵寒风吹来,吹得我直哆嗦。但那个小家伙也没穿太多的衣服——它没有羽毛,包裹它的只有一层 土黄色的皮,倒是有一点蓝色的绒毛,但是太稀疏了,很难分辨出来。我突然萌生这样一个感觉,我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只鸟,但具体在哪儿却记不清了。可它到 底是个什么呢?看它有翅膀,有四爪脚,也有鸟类特有的尖嘴,黑亮黑亮的,身体有山雀那么大,又像是一种鸟类,但它的眼睛却很特别,那是两个蓝色的玻璃片似 的东西,盖在眼睛的位置上,看上去很是奇异,仿佛人造的一般。
这时候风又刮了起来,我只觉得好像有冰冷的钢针打在我的脸上似的,好在我还带着手套,所以我一把抓起了那只“鸟”。这么冷的天,还是先把它弄回车里去,剩下的事情以后再作区处。
就在我把它倒着拎起来时,意外发生了,这只貌似已经死亡的鸟突然醒了过来,疯狂地扑腾着翅膀,不断地挣扎,最后还啄了我的手腕。我因为疼痛立刻把手抽了回 来,它便趁机逃脱了。我看了看我的手腕,袖子上被它啄出一个洞,很快就血渗了出来。我连忙撸起袖子检查,发现那只是一个很小的创口,并没有什么大碍。这时 候我抬起头来,发现那只鸟一直在我的头上盘旋着,并没有逃走,它见我注意到它,便了停下来,浮在半空中。渐渐地我发现它那蓝色的眼睛亮了起来,发出奇异的 亮光。我突然意识到情况有些异常,想要跑开,却已经来不及了,只见一道明亮的光柱从鸟的眼睛里射出来,余光刺得我睁不开眼睛,与此同时,胸口突然传来了剧 痛,感觉就好像皮被撕掉了似的。我已经意识到自己惹来了大麻烦,我一只手捂着胸口,另一只手摸着手枪,我知道我必须要马上打死那只鸟,可我的眼睛什么看不 到——几秒钟的过去了,胸口的疼痛更加剧烈,我忍着剧痛竭力地睁开的眼睛,然而只能看到影影绰绰的一片,什么都分辨不清,又过了几秒钟,我似乎看到了白幕 的中间正有一只黑影俯冲过来,我便立刻举起枪朝上面胡乱地射击,也不知道在些打些什么。接着,那道黑影改变了方向,飞向了别处。它一边飞一边高声地叫着, 声音都是一个调子,像是在传达着什么信息。然而我怎么能放过它?我跟着它的影子继续射击,打了一会儿,只听到一声悠长的惨叫,那只鸟落在了雪堆里,我终于 杀死了它。这时候眼睛也恢复得差不多了,我看到绯红的鲜血从它的身体里淌出来,很快就染红了一大片雪。
我好像死里逃生一样,不论是呼吸还是心跳都急促得很。风依旧刮着,我却感觉不到丝毫的冷意,可我心里传来的阵阵寒意,却使得血液都凝结了。我简单地看了看胸口的伤口,是烧伤,我猜那应该是被激光灼伤的。
“真想不到,那个小东西的身上居然隐藏着这么巨大的能量。”
我走着,忍受着身上各处疼痛,回到了战车里。
当我摘掉黑色的灰质后,一个洞从衣服上显现出来,里面的皮肤已经被烧得没有了好模样,又红又紫,好像溃烂了似的,又有水泡,还有一些粘稠的液体浮在皮肤 上。我不知道如何处理烧伤,虽然伤口一直传来阵阵的疼痛,我也无可奈何。我认为疼是应该的,可伤口终究得处理,究竟该用什么工具呢?我想到《猎人手册》的 里面还夹着伊丽特送的手帕,我便立即找出手册,翻动着书页,最终发现那个手帕果然还在那儿。
白色的手帕依旧很洁净,就好像伊丽特本人。上面娟秀着的小女孩此时笑得很灿烂,我突然发现她是那么美,搞得我都不忍心用这块手帕了,但最后我还是把它敷到 了伤口上,毕竟伤口是不便暴露在空气中的,这虽然是我个人鄙陋的看法,然而手帕敷上去之后我的确感觉舒服了不少,胸口也不像以前那样疼了。
不经意间,c装备上又出现了新的内容,存档机的栏目里显示着光束蜂鸟已被击杀。
“光束蜂鸟?”
我这才记起来,我似乎在马多的猎人办事处里看到过光束蜂鸟的画像,也许是挂在墙上,我也不记得了,那时没有留心。我又仔细翻了翻c装备,还发现了一段繁杂的看不懂的代码,我并不认识它们,也没有过分地留意。
这时,雷达中突然出现了几个不明物体向我的战车靠近。我调整好监视器的焦距,瞄准着那些不明飞行物,这才发现那些只不过是几只光束蜂鸟。它们结对飞行,直勾勾地朝着我这边飞来,一副杀气很重的样子。
“刚才那只蜂鸟胡乱地叫唤,正是在招引它的同伴吧。”
然而无论如何,它们可是自己飞到我的嘴边,不能放过它们。我把副炮的准星对准了它们,毫不犹豫地按动下发射键。
我像是从战火中爬过来似的,那天给光速蜂鸟的那枪彻底暴露了我,于是越来越多的赏金怪物找上门来,我也只好用我的机关炮迎接它们。虽然那些怪物都长得七扭八歪的,却十分弱小,有时候一发副炮打过去,它们便血肉飞溅,肢体被打的四分五裂了。
如此,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困惑——我知道那些赏金怪物有一些智商,它们自是知道自己很弱小,从不会单独来攻击我,这也能看出它们是很聪明的,可是它们既然逃脱不了被猎杀的厄运,何不安分一点,为什么还要不顾一些地攻击人类?这真是一件令人感到困惑的事情。
翻开存档机的菜单,我发现里面已经累积了很多战绩,这几天我一路走一路杀,虽然依旧是单调,可终归有了些乐趣。这是我离开马多的第六天了,六天里我一路向 东行,开始的时候还能看到几座山,后来就只剩下了荒漠,直到现在,四处彻底变成了一望无际的沙漠。天依旧很冷,沙子都仿佛被冻住了一般,显得那么沉,平静 地躺在地面上,不再随着风四处驰骋,但如果有狂风,这里还是会有沙暴的。雪的痕迹已然不多了,它们像是一条条洁白的带子普在沙丘的背面,给这片突兀的土地 做了细微的装点,可还是掩盖不住这一片的死气沉沉。
我也觉得自己没什么必要呆在这里,自从接近沙漠,赏金怪物明显少了很多,也许这里的环境也不适合它们生存。但是,我更关心的是这里也不适合我生存。我所带 的补给只够维持我半个月的生活。现在,十五天已经过去了一半,我不得不考虑原路返回的事情了,如果我的探索没有什么新进展,那我会曝尸荒野的。可是我还是 不甘心,不甘心这么轻易地返回马多。
于是我下了下狠心,决定再往前走一点儿——再走一点儿,如果还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就返回马多。
本文由管理员发布于:2018年01月15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