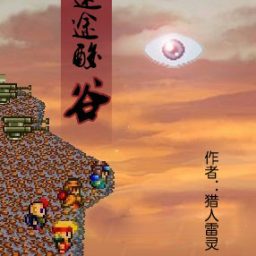《重装机兵之迷途酸谷》第二十章:背叛
夜里不知做了多少梦,我频繁地醒来,又频繁地睡过去,直到我梦见昨天的场景——蔓罗蒂的尸体上盖着白布,有几个人硬要把她抬出去,这时候忽然有人叫我:
“快来看她最后一眼吧,以后再也看不见了。”
于是我走了过去,掀开盖在她身上的白布,发现下面什么也没有。我抬起头,赫然发现门前飘着一个幽灵,那个幽灵似乎是人形,又似乎是圆形的,我已经不记得了,我只记得它看到了我,向我飞来,而我吓得转身就逃走,直到从梦中逃出来。
我被吓得再也睡不着了,看着这个内屋,四周黑黢黢的,没有一点光,没有一点动静,我突然害怕起来,赶快下了床,连外衣也没来得及穿,只想离开这间屋子。
我推开猎人办事处的门,才发现外面天已经大亮了,屋子里很静,只能听到一些毕毕剥剥的声响,原来是炉火正旺,炉子放在那边的休息室里,上面坐着一个铁水 壶,没有声音,只能听到火声。我简单地走了走,这道具店里一点也不冷,当我转到休息处时,我发现昨晚放在长凳上的蔓罗蒂居然不见了,忽然间我的心里发冷, 那种不安感再一次袭来了。
这种不安感其实并不陌生,我似乎经常不安,记得在离开阿梓莎的那天夜里,我就有这种感觉,感觉周围有鬼魂游荡。我似乎经常这样感到不安,经常感到有一个灵魂在跟随着我,我也说不清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感觉,也许只是直觉,但绝不是瞎想。
我正想着,蓝尧突然推门进来了,他见我醒了,跟我打招呼,我回应着他,看到他手里端着一个锅。
“你出去干什么了?”
“拿吃的,卡奇娅烤的红薯,还有汤。”他说着,把炉子上的水壶换成那口锅。
“现在是什么时候了?”
“快中午了。”
我才知道自己竟然睡了这么久。
“卡奇娅呢?”我问他。
“她出门了。你在这里吃过饭,等一会儿也得走了,我会去送你出去。”
这屋子真暖和,那个锅刚在火上放了一会儿,就有了香味,我一闻到香味,突然饿的不得了。
“去哪里?”我知道我是明知故问,于是又补了一句,“那个银牙住在哪儿?”
“他住在下水管理局的下水道里。”
“下水管理局在什么地方?”
“从这里向西走,大概半天就能到海湾大桥,过了大桥再向北走一天,就到了。”
“有没有地图?我从没去过那里,不知能不能找到。”其实我是很怕自己迷路的。
“你拿着bs机就可以了。”他说着,从口袋里掏出了我的bs机给我看,我大吃一惊。
“我的bs机怎么会在你的手上?”
“是金牙给我的。”他说,“金牙今天早晨从你的屋子拿出来的,你睡的太死了,根本没发现吧。她已经把绯bs机上的数据拷贝到你的上面,现在你可以看很多绯曾经去过的地方,另外它已经与卫星通信了,据说可以召唤卫星激光。”
“卫星激光?”
“就是一束从空中射下来的激光,我是没见过,传闻说当年泰德·布罗拉就是败在这东西上的,你应该选一个好天气,找一片没人的开阔地亲自试一试。”
我接过bs机,突然间发觉自己不认识这个小玩意了,它真的那么厉害么。
“你刚才说,绯的bs机,绯难道也有bs机吗?”我问蓝尧。
“当然有。Bs控制器据说只有一个,不过后来又有了两个复制品,就在绯和玛丽亚的手中。”
“那卫星呢?”
“卫星是似乎是勇士俱乐部发射的,是亚马森主要策划的,亚马森是个很了不起的家伙,bs机就是他做的,还做过很多厉害的武器。”
“他都做过什么?”我追问着。
“这个……我也不太清楚,你应该去找一些老勇士。”
他似乎不愿意说了。
后来我就在这里吃饭了,他不吃,只是在一旁说个不停。
他说他已经到地下党的战车大厅帮我把战车补给过了,战车的发电机也坏了,他替我修了引擎,还帮我装了一台暖风机。我被那一锅汤热得脸通红,眼睛里很湿润, 其实我想问他什么来着,可是我也忘记自己想问什么,于是继续吃我的,只听着他说。他说他还给我装了一箱饼干,蔓罗蒂的尸体也放进后备箱了。说着说着,他又 从兜里掏出一个盒子递给我,他说这里面装着金牙的信物,银牙看到后就会相信我,就会跟着我回厄尔尼诺。他似乎说到了重点之处,于是带着一丝催促的口气,说 我必须快去快回,不然一定救不出那个技工。其实我现在对他们充满了感激,看着这个信物时,我就想,无论他说什么我都会去照做。
出城与进城一样,我躲在蓝尧的野巴士上,我的吉普战车被牵引在后面,今天大门的查哨不是很严,我们有惊无险地混了过去,不过我可比上一次紧张多了。
我知道分别的时候到了,可是蓝尧说我们很快还会再见的。我们向西走了半个小时,在一片白色废墟中停了车,其实是一个乱石岗。蓝尧先下了车,我在车上磨蹭 着,本想也找一把铁铲,找了很久也没找到,于是也下去了。当我下车时,蓝尧站在乱石堆里,我走过去时,他正在往一个坑里填石头,他说他刚才找了一个天然 坑,蔓罗蒂已经被放下去了。我看了看四周,这里既没有枯草、枯树,也没有可以遮风挡雨的残垣,只有乱石,单调而又死气。我们想挂一块布做标记,或者竖一块 刻着字的木板,但是转念一想这些东西终究会被风卷走的,于是我们又堆了一些石头,堆成了一座小山,这才使她的墓有别于周围的乱石。
临上车前,蓝尧又把快去快回的事情嘱咐了一遍,我也嘱咐他,这几天要给埃吉鲁送吃的,不能告诉他蔓罗蒂死掉的事情。之后我们就分开了。
看着蓝尧的车走远了,我进了我的战车,把bs机连到c装备上,调出了这里的地图,死死地记下这里的坐标,然后发动引擎继续向西走。
白色的废墟之城,在我的身后越来越模糊,终于淹没在了雾中。那座白色的乱石岗,却在荒原上孤独地守望着,我仿佛看到蔓罗蒂的灵魂站在乱石岗最高处,像一块坚毅的墓碑,没有动作,没有声音,也没有任何表情。
一路向西,是一片白茫茫的雪原。真正的寒冬来临了,这里的雪绝不会轻易融化掉,除非春天来临。
战车似乎跑得更快了,土地很硬,这里的平原也更加辽阔,比起马多那边,这里更有奔驰感。而且我不用再过挨冻的日子了,蓝尧的暖风机很好用,驾驶室里的水也变得温和和的,温水泡饼干也很好吃。
下午的行程有些昏昏欲睡,真是平静的很,即听不到警报,也看不到任何有生命的物体,雷达里静悄悄的。
不知过了多久,雷达的警报忽然响了起来,一段怪物的代码出现在存档机上,我以为生意来了,就让战车靠近警报点,我在那周围转了好几圈,从监视屏里不断地观 察,外面除了雪什么也没有。我索性把战车停到警报点上,拿着手枪下了车,在周围搜了一圈,发现这周围的地面上只有一截枯草杆,那草杆上有明显被剪掉的痕 迹。可是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被存档机报警,我看了很久,想不明白,土冻得很结实,想把这东西挖出来也是不可能的,于是我就继续赶路了,路上又遇到一些相同的 警报,我没有理会。
夕阳低沉的时候,我到了大陆的尽头,远处是沙滩,再远处有一条隐隐约约的河流,目测是一条很宽很宽的大河,真是罕见。我下了车,想亲眼去看看,这个地方真 是静谧,只因为那条河悄无声息地流着,给人一种平静而安宁的感觉。我似乎还听到某种声音,那是一种很深邃的声音,从那条河传过来的,我凝望那里很久,觉得 十分不安,似乎有一个灵魂似的。
回到战车上以后,我从bs地图上寻找海湾大桥的位置,那座大桥就在正南方,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。
夜幕完全降临时我来到那座桥旁,桥头有一座两层的酒吧旅馆,窗缝和门缝里透出幽暗的光。旁边还有一辆野巴士。我在想我竟是住店还是还是赶路,这时酒吧旅馆的门开了,有一个人影忽然晃了出来,他似乎向我喊着什么,我听不清楚,他见我这边没有反应,就走了过来。
“哥们儿,住店吗?”他在外面喊着。
“不住,我去桥的那边!”我对着对讲机说,其实我更诧异于“哥们儿”这种称呼。
“桥封了!桥封了!”他向我大声喊着。
“什么?”我也对着对讲机喊道。
“昨天封的!过不去的!现在这里住一晚上吧!”他说着,拍了拍我的战车。我实在搞不清楚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,因为天已经黑了,桥上的情况我完全看不见,思来想去不如听了他的。于是我就把车停到那辆野巴士旁边,下车了。
“呦,原来是你呀!”
我刚下车,就听到他说了这样的话,我忽然觉得他的声音有些熟悉,仔细想了想,才记起来他就是那天沙漠之虎救下的大胡子。
我吃了一惊,笑了一声回应他。
“你是那天晚上的那个人?……013那天把你扔在这儿了,他一个人跑了?”我随意诌了几句话,来掩盖自己心中的喜悦。事实上我一见到老面孔就觉得高兴,只是不知道这种高兴该不该表现在脸上。
“他已经回沙漠了。”
“这个店也是你的吗?”
“当然了——不是。”他调侃着,“这是一个朋友的店,我在这里呆一阵子,算是被接济一下。”
“那个女的怎么样了——你不是去厄尔尼诺了吗?”他问我。
“进去了,不过又出来了。”
“现在里面乱的很吧!”他笑着,“你难道要去对面避难吗?”
“你刚才说桥被封了,是怎么回事,谁封的?”
我猜这种事一定是掠夺者干的,他却没有立刻回答我,而是搂着我的背,把我抓到屋子里面去了。
进了屋子,热气扑面而来,这屋子里面真是暖和,房子中间就放着一个火炉,四周紧凑地拼着四五个小桌,挤得不得了。那边紧挨着一个柜台,整间屋子只有这么多 东西,剩下的空间都被昏暗填满,而且天蓬还很矮,真是挤得压迫感十足。屋子里只有一盏低瓦白炽灯,吊在火炉上面,似乎我一抬手就能碰到。灯本来不明亮,还 有几个商人坐在那里抽烟,搞得整间屋子乌烟瘴气的,在昏昏暗暗的灯光下,老桌子又油又脏,地面就像个无底洞,没有地板,还坑坑洼洼的,这屋子简直就是一间 水牢,只不过比水牢暖和一点。
我实在想不明白,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简陋的酒吧旅馆。我看到有一个个黑洞洞的地方,那似乎是通往二楼的楼梯,一点灯光也么有,真是瘆人。我本想调侃大胡子,怎么找了这样一个乐园,可是我刚一回头,发现大胡子的胡子已经不见了。
“好不容易逃出那个地方,难道不应该换一张脸吗?”他反问我。
“你怕有人把你抓回去?”我也反问他。
“怕,当然怕。猎人俱乐部那个组织太诡异,我还是能躲多远就躲多远的好。”
闲谈完,我问他正经事,是谁封了海湾大桥。他的回答果然不出我所料,的确是掠夺者。他说掠夺者这次开来不少战车,他分析掠夺者这么做一定是为了抓厄尔尼诺 的地下党,我想,厄尔尼诺的地下党就那么几个人,正在杂货店里活得好好的呢,掠夺者就是一群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笨蛋。我小声告诉他,不如把卡奇娅的行踪告 诉掠夺者,一定会得到不少好处呢,他也小声回答我:“是呀,给掠夺者卖情报的确能获得不少好处,现在掠夺者最缺的就是情报。”
“可是我必须过桥,难道没有其他的路吗?”我问他。
“你还是原路返回吧。”他说,“找个安乐窝,熬过这个冬天,等风声平静了,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”
他说着说着,不知钻到哪里去了,只留下我一个人站在柜台前。
那几个商人们还在静静抽着烟,小声叨咕着什么。而我并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商人把风帽戴上了,蹑手蹑脚地往我这边走来。
我只是在想接下来应该怎么办,我也想原路返回,把这件事告诉蓝尧商量对策,可是我有点不情愿回去。而我又不能不管埃吉鲁,倘若放弃这件事,实在是令我良心 不安,我后悔当初与蔓罗蒂搭讪了,最后落得这种下场,真是咎由自取。我想不如在这里住一晚,明天白天看看桥上掠夺者布下了什么样的阵,倘若有一丝一毫的破 绽,我也要硬闯过去。
我正在这边凝神想着,有人在我的背后拍了我的肩膀,我猛然回身,看到一个比我高许多的人一声不响地站着。我抬头看着他黑洞洞的脸,他的脸藏在风帽里,我根 本看不见他的模样,可是我觉得这种感觉似曾相识,就好像我认识这个人似的。我开始思索,在记忆中搜寻这个非常熟悉的感觉。就在这个时候,那人突然间开口讲 话了。
“桑——德?”
他从嘴里吐出这两个字,是显得多么的生涩,他一定已经很久没叫过这个名字了。我也在喊着,向冲,我还以为你已经死了。我把他搂到了怀里,他也搂着我。他似乎听到我啜泣的声音。
我相信经历可以改变人,但也不会改变得太多,比起一年前,向冲的确瘦了不少,而且我觉得他的身上有了新的味道,虽然我也不知道这种味道究竟意味着什么。
我们在一张小桌上面对面坐下,在昏暗的灯光下,我扣着桌角的木缝儿,其实我对向冲有许多话,我很想知道他这些日子都经历了什么,只是还不知道如何开口。
这时大胡子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,扔下两片餐巾,问我们:
“难道不来点什么吗?”
“来什么……”我哼了几声,我已经忘记向冲喜欢吃什么了。
向冲想了一会,却说:“你们这里不是有十字山谷的伏特加么,来一瓶。”
“伏特加?——是开瓶之后给你们送过来吗?”大胡子问我们,我总觉得他这句话问得很奇怪。
“不用不用。要么,您先去忙吧,你看天都这么晚了……您就告诉我伏特加放在哪儿,等我们想喝的时候自己去拿,退房时你就算到我的账上!”他的语气忽然变得很客气,就好像演戏一样,这真是叫我吃惊。
“酒就放在二楼的酒架上,上楼梯就能看到,伏特加只有几瓶,字也很显眼。我就不管你们了,记住只要开瓶,明天就得给我付清酒钱,我可不想惹上赊欠高价酒的事儿。”大胡子轻佻地说着,我感觉他这句话不是说给我听的。
“不一定喝呢!”向冲轻轻地说,温和地笑了起来。
“还是算到我的账上吧!”我见大胡子要上楼,急忙站起来把他喊住。
“你还是跟他算清楚的好,别等到明天其中一个偷偷跑掉了,另一个有嘴说不清。哈哈哈哈……”大胡子大笑着,还是走了。向冲也在椅子上冲我嘿嘿地笑,只有我 还在傻傻地站着。我只是在想这件事情被向冲弄麻烦了,只是吃个饭而已,弄这么多场面多麻烦。我想把这句话说给他听,后来想还是继续装傻算了。我忽而想起十 字山谷的伏特加也是霞大姐钟情的酒,那种酒似乎喝一点就会醉,向冲要喝这种酒,难道他也偏爱它么。
我正想着,向冲突然向我发问:“我说,你最近在哪儿发财了?”
此时我还傻愣愣地站着,我没想到他会提出“发财”这种话题,支支吾吾地哼了一句:
“发财?哪儿有什么财可发……”
然后我就坐下了。
我双手抱胸坐在椅子上,眼睛似乎盯着桌面,其实我也在用余光偷偷地观察他,他也在用手指头扣着桌面这块烂木头,我猜测他也一定在看我,也想从我的嘴里知道 一些事情,正在想话题。而在这短暂的重逢之中,感动之余又有失落,我嗅到了向冲身上世故的味道,因为我对他有很强的戒备感——对陌生人的戒备,就好像第一 次见到霞大姐的那种感觉,不过他也是那个曾经陪我在阿梓莎度过一个个清清冷冷的日子的人,我没有忘记那些事情,曾经是苦日子里有纯洁的情感相伴,现在纯洁 被他那张戴着面具的脸驱赶得一去不复返,我觉得心里很不舒服。现在的他与一年前的他已然不是同一个人了,我想着,心里又哑然一笑:自己何尝不是如此呢?
“你知道——伏特加多少钱一瓶么?”他又向我发问。
“不知道。”
“既然不知道,难道不想问问?”他问我,“我见你刚才争着抢着要买单的样子,还以为你是在买伤药呢!”
他这句话我是听明白了,他是在嘲讽我,我想着,沉默不语。他见我不理他,又问我:
“你做猎人这么久,难道不泡酒吧么?”
“不喝酒。没有钱。”
他听我这么说,大笑起来。“你这么说我可不信,我做游商这么久,还从没见过穷猎人,难道你是我生平遇到的第一个?”
我实在觉得无话可说,我想了一会儿,问他:“向冲,你就这么好奇我有没有钱?”
“不要把话问得那么直白嘛!”他又温和地笑了起来,他真是戴着一张面具。他对我说:“不过我们毕竟是朋友,既然是朋友,这么久不见,总得互相露个底儿吧!”他想了一会儿,又说,“反正我跟着商队吃大锅饭,兜里面空空如也,不信你来摸!”
“哼,你还记得我们是朋友。”现在轮到我嘲讽他了。
“记得,当然记得!”他说,“不过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,我已经忘的差不多了。”
“我也忘的差不多了,所以才想跟你说一说。”
“呵……说那些干啥?那些记忆已经在这一年的风吹雨淋中消磨得一干二净了。我说,你一定也是经历过一些事情的人了,为什么还那样天真呢!”
“天真?”我笑了起来,实在觉得无话可说。他也闷在座位上,过了一会儿,又是他先开口问我:
“看你的样子,不如来我们商队做保镖,很多猎人都靠这个吃饭的。我们付给猎人的钱虽不多,不过总够你吃上一口饭。”
“谢谢——”我这算是感谢他的真诚,“我有饭吃,饿不着。”
“难道是我小看你了!”向冲的口气又变得浮夸起来,“我听说不死女战神前些日子死在马多了,我记得你跟那个人……”
“她是我的姐姐。”我很不耐烦地提醒他。
“哦,对对对,你是他的弟弟,这件事很小的时候你就跟我提过。”
他见我还不说话,想了一会儿,又问我:
“你是怎么从阿梓莎到的马多?”
“她把我带去的,然后她就死了。”
“之后你就当猎人了?”
“当然!不然的话,我如何活到今天?”
“杀过多少赏金怪物?”
“没数过。”
“杀过赏金首么?”
“当然,比如沙鲛。”
“哦?”他很惊讶,“你杀死了沙鲛?那你现在就是个富翁了!怪不得呢……你的话为什么这么少,原来你这样横!你是瞧不上我这个做游商的朋友了。”
我实在是无话可说,也不明白向冲究竟在想些什么。也许真的是经历改变人,使我们很难再相处。此时我起身想离开,他忽然跳起身来拉住我。
“你要干什么去?”
“我去睡觉!”
“店主已经休息啦!”
“那我就把他喊醒。”
我执意要走,他却抓着我衣服的后襟不让我走。
“你先别走嘛,刚才我说的都不对,你别生气好吗?就像你说的,我们坐下来说说以前的事。”
他是数狗脸的,我算是领教到了,他这样闪烁其词,我开始想他葫芦里究竟要卖什么药。
我被他按回到椅子上,我闷在座位上,一句话也不想说。我知道接下来一定又是他向我发问,我已经厌烦了,于是这次我先开口说话了:
“我不想陪你说了!”
“那我们要点吃的?”
“你不是说店主已经睡了么?”
“那我们喝酒吧!”他欢快地说着。
“喝酒?喝伏特加么?”
“当然喽,你不是没喝过酒么,这就算是第一次,放心吧我是不会让你买单的。你第一次喝酒就能喝到高价酒,还有你的老朋友陪你,陪你一起叙旧,这不是很爽的事情么,你说是不是?”
我没理他。
“你别动,我去给你拿酒。你可要老老实实地坐在位上——等我!”
他说着,站起身来。
“你可不许走,走了你就不再是我的朋友了!”
他又向我念叨了一遍,然后就上楼去了,只留下我一个人坐在这个昏暗的大厅里。
四下忽然间变得沉寂的很,我看了看周围,才发现刚才那群游商早已经不知去处,大厅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。刚才还他们坐在灯下面抽烟,现在人散了,烟也散了, 白炽灯忽然发亮了许多,那些被灯光照亮的地方愈加的清晰起来,而那些灯光照不到的地方也愈加黑暗,黑得深邃,黑得没有一点颜色和一点声音,令人心中发冷, 这种纯粹的黑暗倒是让这个夜变得凄美起来。我才发现,没有朋友相伴的日子,就像这个夜一样,冷冷清清的。
我坐在椅子上等着向冲,不知过了多久,一个游商拿着一瓶酒从二楼走下来,径直走到我的对面坐了下来。我抬起眼睛看了一眼,竟然是个女孩,长得还算漂亮,瓜子脸,五官很标致,只是有点瘦。
“小哥儿!”她叫唤着我,声音很好听,“你就是冲儿的兄弟吧。”
“冲儿?你是说向冲?那你是……”
“我是冲儿的同伴。”那女孩十分平静地说。
“向冲他人呢?”
“他说他去找店主点菜去了,他让我陪你先喝几杯,等会儿咱们吃顿大的——怎么样,小哥儿,不喝几杯么?”
“不了,我还是去找向冲吧!”我实在觉得她太热情了,想溜掉。
“哎!小哥儿,那个死鬼有什么好找的,陪我坐一会儿喝杯酒,不好么?”
我总觉得这个女孩是向冲的女朋友,我说:“这有些不方便吧。”
她却说:“这有什么不方便的?同是天涯人沦落人,相逢何必曾相识,遇上了是缘分,既然有缘,喝喝酒,说说话,又有什么不好的?”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坐在椅子上,心想这女人真是不简单。
她倒了两杯酒,递给了我一杯。我想起霞大姐喝了十字山谷的伏特加之后说胡话的情景,忽然间不敢喝了。我把她递过来的酒杯放在一边,说:“酒先不急着喝,喝醉了就吃不成饭了,要不然我们先聊一会儿?”
她正端着酒杯,听我说出这种话,显得有些诧异,不过她还是冲我笑着。
“你说什么,咱们就聊什么。聊一句喝一杯酒怎么样?”
我一直在想向冲刚才奇怪的样子,在想他为什么能说出那些话,并没有在意她的话,我直截了当地问她:“向冲在你们商队是干什么的?”
她听到我的发问,有些犹豫了。
“你问冲儿,冲儿他呀……他就是一个打杂的。”
“打杂的?”我有点不相信,发出了疑问。
“其实……也不是……”她又回答得含糊其辞的。
“他每年赚的钱——足够养活他自己么?”我一边想着一边问她,不过我又觉得自己的话没问清楚,于是我又补了一句,“他平时靠什么赚钱?”
“啊呀,小哥儿,你怎么总是问这种问题?”她对我说,“你问游商能不能养活得起自己,又问游商平时靠什么赚钱,这些问题也太……”她的语调开始上扬了,她似乎马上就要说出什么,又被她咽了下去。不过她刚才的情绪很激动,即使她什么也没说,我也察觉到了。
而我把语气放缓了一些问她:“我刚做猎人不久,对外面的事情不太了解,你给我讲讲呗。”
听了我的话,她窘迫地笑了起来,似乎是说“无话可讲”,她刚才的精神劲儿全然消失了,她只是低着脑袋,闪避着我的目光,似乎在思考什么。她默然了,而我更好奇她为什么默然了。
“来来来,猎人小哥儿,喝酒吧!喝酒吧!”只过了一会儿,她又提起喝酒的事。她索性站起身来,走到我身边,把我挪到一边的那杯酒拿了起来,直接塞到我的面前。
“一定要喝吗?”我有点疑惑。
“一定要喝!”她回答着,翘着她很秀气的嘴,“没有理由!”
可我还是不想喝,我接过她的酒杯,装出一副很犹豫的样子,“可是,这酒喝下去就迷糊了,迷糊了就吃不成饭了……”
我正说着,突然听到“砰”的一声,她的酒杯掉到地面上。我的心中一惊,立刻去看她的脸,不过我发现她的表情并不多,还是翘着嘴角笑着。
我问她:“怎么了?”
“一不小心把酒杯碎了……”她如是地说,像一块木头戳在原地,只是她的表情依旧很自然,
我只好弯下腰去,去捡起地上的酒杯,酒杯并没有碎,酒撒了一地,我发现地面上那一滩酒居然一点味道也没有,可是我明明记得当初在霞大姐旅馆的时候,十字山 谷的伏特加酒只要开瓶就能闻到香味,现在这酒已经撒了一地,怎么一点香味也没有呢?我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头。我把酒杯递给她,问她:
“究竟拿的是什么酒,不是伏特加酒吗?”
我只是随口一说,她听了我的话,忽然满脸惊惶,我看她是要张嘴说什么,可是她的脸开始颤起来,她不再笑了,表情变得非常奇怪,她用双手捂住脸,不想让我再 盯着她看,可是她的腿忽然软了,一下子瘫坐在地上,她嚎啕大哭起来,并且捂着她的脸。我就在她旁边,被她瞬间的变化吓到了,我连忙蹲下身去问她:
“你怎么了?”
我接连问了好几句,她只是哭着,也不回答我,我总觉得事情不妙,于是冲她吼了一句:
“你到底怎么了!你们到底想对我做些什么?”
她听到我的吼声,身体猛烈地颤抖了一下,她突然间不哭了,用手擦去她的泪痕,抽噎着对我说:
“你不要杀我……我什么都可以告诉你……”
“杀你?”我惊愕地反问她。
“酒里有**,向冲要杀你!你快逃——你快逃啊!”她说着说着,脸上的肉都挤在了一起,她开始哭起来。
“杀我?他凭什么杀我?”我对她的话感到莫名其妙。
“他去大桥找掠夺者了!他说只要把你交给掠夺者,就会得到很多钱,现在他一定已经找到掠夺者了!”
我被她的话惊出一身冷汗,我只是愣愣地想着从前的向冲,气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。她看我还蹲在地上,急忙冲我喊:
“你快逃啊!——你快逃啊!”
她还拥了我一下,我看着眼前这个泪人,气得狠狠地打了她一拳。我站起身正要逃出去,可是她却抓住了我的衣服。
“不行啊!你别走——我是被逼的,你逃走了冲儿回来也会弄死我啊——你带我一起逃走吧!”
我用力挣脱她的手,可是她的手像咬住了我一样怎么也挣不掉。
我只好狠狠地这条疯狗踢到一旁,她终于躺在地上不动了。我急忙蹿出屋去。
我来到外面,四处一片漆黑,还没有掠夺者的影子和声音。我上了战车,心里终于踏实了一些。
就在这时,我听到外面传来那个女人的叫声。她到底是跟了出来,她跑到我的战车前砸我的门,声嘶力竭地重复着一句话:
“把存档机拔下来——那东西会暴露你——把存档机拔下来——那东西会暴露你——”
我的心有些软了,犹豫了一会儿,打开车门下了车,想把她塞进后备箱里。她却上气不接下气地说:
“如果你信我,你就跟着我,在这空旷的原野上你终究是逃不掉的。我知道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,我开他们的车——你要跟紧我!”
她说完就跑上了一那停在门口的野巴士,她开着车蹿了出去。我也顾不得三七二十一了,拔下存档机的线,跟着她的车一同逃了。
本文由管理员发布于:2018年01月15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