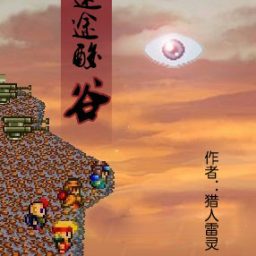《重装机兵之迷途酸谷》第二十五章:与霞大姐的重逢
今天收到了伊丽特的传真。
桑德:
我们听猎人办事处的人说,你消灭了大沙漠里的沙鲛?你没受什么伤吧。我们现在一切都好,试验田修好了,也有游商和猎人来镇子,我现在正在爷爷的修理店帮忙。我知道码头镇有直通马多镇的联络船,不知现在还有么。
你现在怎么样,能回马多镇么?
伊丽特
没办法,我只好下楼去猎人办事处又送出一封短信,信发完,忽然想出去走走了。
这里的猎人车店更像是由一座城堡改装而来的——主体是一个五层左右高的锥形楼顶的石头建筑,下面镶嵌着各种方形小楼,就好像一位保守的僧侣身上突起了数不清的摩登毒瘤,看上去一副不伦不类的样子。
至于城堡的里面,除了先前提过的走廊、瓷砖,还有一条条木质的楼梯扶手,木柱上雕刻着各种各样曲形条纹,看上去甚是美观,只是那扶手已经被磨得破败不堪 了,我猜那一定是一块十分精美的木料,现在却好像被老鼠磕过似的——被猎人们摸坏的吧。我信步地走下楼梯,随处望着,从长满疮疖的墙一直望到大厅中央顶部 的吊灯,我似乎还看到了烛台,烛台上装着电灯泡。我想,这座遗迹究竟有多少年的历史了?
我走在通往码头镇的路上,迎着寒风,心情豁然开朗——很久没有像今天这般走路了。因为昨天下了雪,四周又是白茫茫的一片,忽地想起了那次徒步遭遇光束蜂鸟 差点丧命的事情,自己在茫茫雪原上想着想着,独自笑了起来——谁也听不到。远处,沙尘的迷雾已然消失,那些荒凉的野迹越发变得清晰起来,我看了很久(因为 没有别的好看的)那些野迹不是坍塌的,就是被掩埋的,零零落落地散布码头镇的周围——与厄尔尼诺的断壁残垣完全不同,这里的一切似乎是沧海变迁的结果。
我的面朝东方,金色的海平面映着朝阳的光辉,渐渐变短,一座一座的屋宇从地平线上升起来,变得越来越纷繁——都是房子,有什么好看的?我想着。这次出门, 我并没有告诉埃吉鲁和卓娅,因为他们两个早就溜走了,野巴士也被开走了,而我的越野车暂时不能用,我倒是宁可步行到码头镇找他们,或者索性散步。
在这种没有狩猎的季节,我便成了多余的人。
码头镇外围也有石头城墙,并不高,似乎是城堡的附属物,只是顶部的铁栅栏非常漂亮。大门似乎只有一个,宽度能够容纳并排的三辆车,两边的门垛上还装着球形 的灯,似乎让我想起了什么。我蓦地发现我曾经来过这个地方,当时也是从这个大门——两边的球形灯放着异常明亮的光,我在一条冷冷落落的街上,跟着玛丽亚, 却总是追不上她的步子。我至今还记得玛丽亚催促我快走的声音,现在想起来,那声音似乎不止一个——
现在,我的前方就是那条笔直大路,大路的尽头是码头,有几艘小船静静地停泊在那里,海水平静而又暗淡,风声也消失了,仿佛时间凝固了一般。一种奇妙的感觉 再一次袭来,无论是从我的记忆深处还是眼前的现实,我看到那片无尽的海水蒸腾起来,那些水汽仿佛都有了思想,凝成了一个意识,似乎正在用一个硕大的眼睛观 察我,它要向我发问,然而我们之间如同存在着生与死一般的不可逾越的隔绝,我既无法看到它,我也无法听到它的声音。
远处传来一阵轰响,我感到时间正在颤抖,轰然间崩坏离析。我猛地回头,看到一辆装甲车驶向远处,传来悠然的声响。等我再次回过神来时,街上的行人忽然多了起来,风也吹起来了,夹着许多人的嘈杂声,我站在码头镇的门口,感到些许寒意,刚才的幻觉已经得无影无踪了。
于是,我只好继续向前走我的路。
码头镇的主镇是不允许猎人的战车进入的,也就是我的前方与右方,猎人们大都进城左转了——穿过一条小径,北面有蚂蚁们集聚的集市。我向前直走着,因为我是徒步来的,我想去尽头处的小码头看一看。
小码头是用木排修成的,那里只有几个小游艇,远处还有几艘比较大的客船,死一般宁静地停泊在别的小码头。走下木排,还有一些用油桶和木桩绑成的浮桥,我跳 了过去,站在木桩上望着水面发呆——四周的海岸都有结冰,这里却没有,只是漂着一些细碎的冰凌,说明这里还是经常有船通航的。
我正想着,远处冒出来一艘天鹅游船,我看着它缓缓前行,好像一座移动小旅馆朝这边游着。终于就在我的旁边停下了。我站起身,仰头望了望,那天鹅头居高临 下,只投下一个硕大的阴影——我居然连它的眼睛都看不到。看这艘天鹅游船的外表并没有破损,似乎是一个远离战火的处所,我忽然心驰神往起来——我还不清楚 海上的情况,如果那里还没有被掠夺者侵略,倒是很想去看看。
不一会儿,有人从里面三三两两地走出来,其中还有些猎人扮相的男女,我在一旁看着,忽然想起了卓娅。
他们的人走得差不多了,我也想离开了。我蹦回到码头上,稍有留恋地回望,我现在在用另一种角度看它,透过侧面的圆形小窗子,我看到里面还有白漆的小桌子,有吧台,还有楼梯……
我正看着,忽然发现天鹅船里面还有人,并且注意到了我似的,我赶忙把目光移了开,把身子闪到了一边去,跳到木排的边缘打算就这样溜掉了。只是刚走了几步, 忽然觉得天鹅船里的那个人影总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。我还在想着,身后传来有一只脚踏在木排上的声响,听那声响很有重量,是有什么人出来了。
“桑德?”
我居然听到有人喊了我的名字,而且那声音很熟悉,我回头一看,居然发现那是霞大姐。她穿着一身咖啡色的制服,端庄古朴,若不是她还是那副憨态可掬的样子,我都不敢认她了。
“霞大姐?”我也做着惊叹口气,事实上我完全表现不出霞大姐那样喜悦的神情,也许是疲惫和无奈的表情在我的脸上寄居太久,心里的喜悦却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了。
“进来!进来!”她向我招着手,笑着。我看了她一眼,像她那种年龄的并且了无牵挂的女人,自然有条件活得轻松一点,而我实在无福消受她的幸福,我又在胡思乱想着。看我愣在原地,她便走了过来,把我拽进了天鹅船。
天鹅船里是一个标志的立方体,所有墙体都粉刷着白色,几乎没有其他装帧,只有黑色的笔挺挺的边角线和一盏镶嵌在天花板里的方形灯具,地面则是淡淡的浅灰 色,很摩登。我坐在了一个靠窗的位置,船内稍稍有点暗,于是窗外的景色就变得很明亮起来——淡蓝的海水,淡蓝色的天,海平线上薄薄的白雾,我似乎还望到了 一些岛屿。这时候,有音乐响了,是一首悠长而轻快的曲子。
“里奥拉多有一座小屋
住着奇怪叔叔
小屋下面有一片空地里
是一棵大树……”
“这是什么曲子?”我问霞大姐。
“随风而逝的记忆。”她说,“马多的一个同开旅馆的好友送给我的。”
“他是不是叫雷班纳?”
“你也认识他?”霞大姐笑着。
“没有,只是说过几句话……”
霞大姐端着两个杯子走了过来,在我的对面坐下。
“听着他
讲述着那些欲哭无泪的
难忘的往事啊
在那里,孤独地流浪啊
人们啊,怀念那些欲哭无泪的
回忆啊,随风儿飘走了……”
听着曲子,不知为何思绪纷飞了起来,海平线那边的薄雾依然在静静地徜徉,我不知不觉把头撇向了窗外,因为眼眶有点湿润了——我忽然想起了曾经发生过的许多事情。
霞大姐坐在我对面,不知她是不是在观察着我。于是我故作着镇定,把头转了回来,我举起她带来的一个杯子——里面好像只是饮料,问她:
“这曲子是雷班纳本人唱的么?听声音很像。”
“是雷班纳唱的,据他说是别人写给他身边的明奇博士的。”
“明奇博士?那个很有趣的老头儿?”我问着,脑子里浮现着那个老小孩模样,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“就是他,总觉得不太像。这歌好像是给那种心中有不可释怀的郁结的人写的。”
霞大姐说完,开始喝她的饮料了。我也随着喝了几口。
“你什么时候来的码头镇。”霞大姐说。
“最近才到的。”我答。
“赏金呢,收到了么?”
“收到了,”我笑了起来,“早就收到了,如果没那些钱,我也活不到现在。”
“我还以为与你只是一面之缘,看来人与人的缘分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。”她笑着,“我刚来到码头镇,就听说海湾大桥被封锁了,你是怎么过来的?”
“从一条地下隧道里……”我回答。
“嚯嚯,还有那种地方……像你们这样的猎人,总是能制造出那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来。比如沙鲛,我曾经委托过许多猎人——包括沙漠之虎去围剿它,结果都没有成功。没想到最后它居然死在你和我的手里了。”
“沙漠之虎因为这件事,很器重你的。”她说着,“对了,他找到你了么?”
“我们见过了,在厄尔尼诺镇多亏了他的关照。”
“哦哦哦……”她答着,若有所思。
霞大姐起身,又去弄了些饮品。而我实在觉得刚才的饮料里掺着酒,这会儿,肚子有点不好受。
“我想要点水!”我向霞大姐喊。
待霞大姐坐下来,我们之间的对话又开始了。
“其实在那个bar&inn,我就发现你对沙鲛的那些……”我不知该如何提起这件事,可我又很好奇,“我记得在你的房间里放着一张照片,上面有个男人……他是你的……”
“亡夫。”霞大姐支着下巴看我,她那一脸的波澜不惊好像在说:“你接着问吧。”
“他去了多少年了。”我问。
“十一年。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啊。”她叹了口气。
“您现在也不老。”我说。她把眼睛眯起来,只是摇着头笑着。过了一会儿,她说:
“当初啊,还是总部要分配勇士到周边城镇的时候,我和我丈夫被分配到了马多镇。然后就在前往马多镇的途中,越野车被沙鲛追住了,车子被撞翻,我摔了出去, 我的丈夫连人带车被埋在了沙子里,等我把他挖出来的时候,他已经死了。后来我失魂落魄地来到马多镇,雷班纳先生收留了我,我在那里住了半年,也曾经重操旧 业想去杀了沙鲛,然而都失败了。那时,总觉得自己实在给人家添了太多的麻烦,于是我管雷班纳先生借了一些钱,在沙漠深处建了那个小 bar&inn,就这样一个人独自过了许多年。”
她讲完了,很平静,我什么也没说。
“杀掉它之后,你心里是什么感觉?”我望着她,不知为何冒出这样一句。
“没什么感觉。”她摇着头,“其实很久以前就没有感觉了。我在那个旅店生活了许多年之后,心中的仇恨早已经泯灭了。只是……那可是我的丈夫,我们曾经相爱、生活过……唉,那些事情又怎么能轻易忘掉呢。”
她不知叹了多少口气,语速很缓慢。
“我一直在劝自己,不要让自己在仇恨中陷得太深。不过你也看到了,那个山谷里有许多机关,那是我当年布下的。杀掉沙鲛之后,我有点万念俱灰的感觉,我先联 系到了沙漠之虎,我们一同去了厄尔尼诺镇,不过沙漠之虎打听到掠夺者马上就要戒严了,没办法,我只好独自逃到了码头镇,好在这里还是一如既往地太平。”
“其实我更想知道的是——沙鲛伤害人类么?”
“它当然不伤害……”霞大姐苦笑着,“沙鲛吃赏金怪物,它对人类中立,这些也许只有我知道。当初是那些猎人觉得沙鲛吃掉的赏金怪物太多了,于是才去招惹它,沙鲛就变成赏金首了。”
我听着她的话,仿佛回到了若干天以前——我与沙鲛作战的那一天,沙鲛在我身后发出的那种近乎于撕心裂肺的叫声,仿佛哀鸣,我总觉得那不绝是一个“怪物”所能发出的声音。
我陷入了沉思,那种深陷迷雾之中的感觉再次袭来,我隐隐约约地感知到周围的世界存在着许多蹊跷,然而我还无法看清这些。
霞大姐见我神游起来,就接着说下去:
“当一个人孤独无助的时候,他身边的无所谓是至亲还是仇人,都会变成相依为命的朋友的。你总有一天也会体味到这些,桑德。”
我听到她叫我的名字,不由得回过神,哼了一声:
“……唔,我还理解不了这些。”
“总有一天会的。为了你曾经的亲人、朋友,或是其他的什么。”
不知为何,我开始对霞大姐的话题产生了反感。我不再吱声,独自沉默着,而后想,这样僵着不是办法,不如说一些客套话尽快脱身。
“霞大姐在这里做什么?你的这件衣服看起来真标志。”我便客套起来。
“在给码头镇的bar&inn管理天鹅游船。如你所见,这不是很棒的工作么,那边有渔场,有金色沙滩,还有一些被驯服的赏金怪物在这里生活,总会有人来这里度假……”
“被驯服的?”我问。
“不攻击人类的那种。”霞大姐说,“最重要的,这里有海,我一看到海水就好像能看到一种有灵性的东西,我很喜欢这种感觉。”
我本来想说,我也有这种感觉的,不过最终还是保持沉默了。
我们寒暄了几句,就到了霞大姐工作的时间,她开船出航了,我虽然还可以多呆一会,不过我找了借口离开了——我说我的同伴还在猎人车店里等着我,下次我们会一同来坐天鹅船。
事实上嘛,同伴们早就把我抛在一边,自己出去玩了。等我告别了霞大姐,走出了天鹅船,又被这冬日里煞人的严寒所包围的时候,我忽然想起马多镇了。其实早晨的时候,我给伊丽特回复的那封传真是这样写的——
伊丽特:
我现在就在码头镇,我还不太了解这个镇子,等一下我回去码头附近打听一下联络船的情况。我一直都很好,也很喜欢这种漂游的生活。这个冬天我和同伴们要在码头镇做一些买卖,春天打算去狩猎赚钱,近期可能无法回去。切勿思念,希望你们在马多镇好好保重。
桑德
这便是口是心非的表现之一吧。我发现在这个奇怪的世界里,内心与现实的矛盾已经越来越多了。
本文由管理员发布于:2018年01月15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