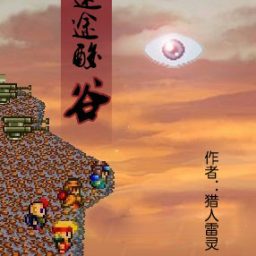《重装机兵之迷途酸谷》第十三章:霞大姐的旅馆
我对自己现在的驾车技术还是很有信心的,我的操纵能力要比刚出来的时候熟练多了,即使在夜里赶路,也没什么好担心的,即使碰到更难处理的麻烦,那也无所 谓,赏金怪物的出现等同于送给我更多的赏金,我已经杀了很多的赏金怪物,我还得去猎人办事处领取赏金呢,一想到自己马上就要得到有生以来的第一笔可观收 入,我就激动得很。这可真是一种令人振奋的愉悦,像是兴奋剂一样,使我的困意退去了很多。顶着漫天的星辰,我驾驶着加西亚号继续往东方驶去。再勤快一些, 就能回去领赏金了。
我已经赶了一夜的路,现在正是凌晨,天还没怎么亮。我看着监视器里,远处的景象也是模模糊糊的,渐渐的,我发现远处升起了一道的围墙,我把物象拉近了一 些,看到一片山群的轮廓。再走近了一些,我发现的确是一片山群,山峦的起伏很大,有的地方高耸,有的地方凹陷下去,中间的位置有一个缺口,像是一条山谷。
我在犹豫着——究竟进不进去。好奇心驱使着我进去看看,因为山谷里面依旧是沙漠,看上去稀松平常的样子,似乎没什么危险。然而我又怕浪费了燃料,最后回不到马多镇。我矛盾了好一会儿,还是决定进去看看,如果在天亮之前没有什么新发现,我一定老老实实地原路返回。
车子被开进了山谷,我只觉得引擎的杂音变得更大了,也许是因为两侧高耸的山产生了回音,而回音加大了引擎恼人的声音。在车灯的映照下,我大概地看了看这些 山的面貌,这些山上覆盖着很少的沙子,多数都是些嶙峋的岩石,每一块似乎都与水平面垂直,一块磊在另一块的上面,直向天空的方向插去。在一些岩石缝里还有 些小植物,稀稀疏疏、零零落落地散布在峭壁上,干枯的枝丫散发着铁青的颜色。
行驶了不久之后,山谷开始向南延伸,顺着这个方向刚走不远,我便出了山谷,来到了一片新的开阔地。天还黑着,我并不能看不清这里的状况,但是凭我的直觉, 我认为这里很宽阔。这时候,雷达里突然侦测到不明物体的移动,我还以为是赏金怪物,一边看着监视器里的漆黑一片,一边抱怨着赏金怪物怎么会在夜里出现。可 是这回我是我判断错了,雷达显示出与以往不同的信息——一个存档机的代码。既然是存档机,我想那个不明物体一定也是猎人了,都是同行,应该没什么危险可 言。过了一会儿,我若无其事地看着一辆装甲车从我的身边驶去,我没有理会它,继续探索着这片未知土地。
我继续走着,突然看到一个微弱的火光,直觉告诉我那是由人类造出来的,我的心里一阵欣喜,顺着火光的方向追寻着它。然而就在我离那道微弱的火光越来越近 时,它却在夜幕里消失不见了。我满心遗憾,心想我进山谷的决定也许是错误的,忽然间一个巨大的建筑物出现在了我的面前,让我吃了一惊。我用车灯晃了晃那栋 建筑物——是个酒吧旅馆,我看到墙上面标注的“酒吧旅馆”的字样,并且还有一个箭头,示意我往右走。顺着那个方向,在灯光的指引下,我发现了前方的一大片 覆盖着沙土的宽阔空地,走近时我又看到了满地的车辙,我猜这里应该是个停车区,想必刚才的那辆装甲车就是从这里离开的吧。我把车停在里面,又用车灯在此确 认一下那栋建筑物,那是个双层小楼,样子真好像马多的那栋酒吧旅馆,但似乎要更大一些,整栋楼没有一个开着灯的房间,也许人们还在睡梦中,在车灯的映照下 我看到了旅馆的入口,就在停车区的旁边。于是我下了战车,锁好车门,摸着黑决定进去探一探。
推玻璃门,依旧是漆黑的一片,里面没有开灯,什么都看不见。这种未知的黑暗往往给人一种莫名的神秘感,令人感到恐惧,可我已经赶了一夜的路,已经疲惫不堪 了,直到现在两个眼皮还在打架,我迫切地想要找到一个舒服些的地方休息一下。作为人类,我能充分感觉到这里有人类的气息,然而这里的老板却不知所踪。此时 的我多么想交上10G的住宿钱,然后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啊,我这样想着,又打了个哈欠。
我有点站不稳了,便想找个凳子歇一会儿。这时候天稍稍亮了一点,我走到大厅中间,发现这里的视野挺开阔,所以就站在大厅中心四处打量着。虽然这里静得出 奇,也没能看到人类,但在吧台上还剩下许多玻璃酒杯,我凑了过去,看着那些杯底被漆过的杯子,在这种太阳还没有升起的黑夜里,它们红红绿绿的颜色此时显得 黯然得很。大厅里还能看到许多桌子,上面有一些小菜,多数只剩下油腥腥的菜汤——这些可是我特意注意到的,因为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一顿像样的饭了,有些馋 了。这里似乎刚举办完一场聚会,还有些喝剩下的酒瓶零零落落地摆在地板上,跟那些酒杯和盘碟一样,让我感觉到当时的热闹气愤。只可惜这房间里没点灯,很多 东西还是看不清。
“一个如此规模的旅店酒吧,怎么会没有灯呢?”我自言自语着,抬起头来,看到了头顶上有一盏奢华的吊灯时,一些无聊的想法才就此打住。
我靠在吧台边上,端着一个高脚杯观摩着,那酒杯里还剩下些酒,我摇了摇杯子,这些清浊的液体瞬时便激荡起来,我猜测此时这种麻痹人的东西一定很凉。
在这种夜里,总觉得四周黑得空空洞洞的,这屋子里也是静得出奇,除了我的呼吸声,再听不到别的声音。这里应该有人,但是一旦这里的主人看到我唐突地出现在 这儿,他会怎么想呢?认为我是贼么?我当然不是贼,但我总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些鬼鬼祟祟的,毕竟自己进来的时候连门都没敲,不过即便我敲了,又有谁会听到 呢?
呆着也是无聊,我便起了好奇,摸着黑在这个大厅里游荡起来。这里的构造并不是很繁杂,进门之后,右面便是一个硕大的吧台和一排吧椅,左面是很多就餐用的小 桌子,角落和桌子之间的缝隙里似乎还有些装饰物,走进时发现是一些大叶植物,摸上去好像橡胶一样。我只注意到这屋子中间的顶部有一盏吊灯,不知道是什么材 质的,但是吊坠很多,看上去很是奢华,但并没有找到开关。往大厅的深处走走,看到了一面墙壁,墙壁好像还贴着壁纸,但我看不清是什么颜色,在那堵大墙上似 乎还挂着一幅壁画,同样看不清具体的模样,只是觉得那上面好像画着什么绯红色的东西,在这种昏暗的夜里,也只能分辨出一片暗红的颜色了。
就在这时,我的耳边突然传来隐隐约约的声响,然而太微弱了,近乎分辨不出是什么声音,但我还是保持着十足的警惕。我绝不是担心着出现赏金怪物,我只是害怕 这声音是这家的主人发出的,我真的怕他误会我是个贼,因为我知道总会有那种胡搅蛮缠的人,然而我又向来不会对付这种人,我总不能一枪毙了他——我们毕竟都 是人类。可那究竟是什么声音,又是从哪儿发出来的呢?我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,就是我左手边的方向,原来那里还有一个走廊,同样是黢黑一片。可是渐渐 地,那个声音悠悠扬扬,向我这边飞来了——是拖鞋趿地板的声音,我立刻就辨认出来了,他是想到大厅来啊,若是他看到我在这儿鬼鬼祟祟地站着,一定会起疑心 的。于是我立刻踮起脚,缩着身子,尽量不发出多余的声音,疾步地蹦到大门口,然后装出了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,我想这样的对策应该能蒙混过关,虽然我这是在 耍小聪明,担着一丁点风险。
等了一会儿,那人终于要进大厅了,只听见他在走廊的尽头止住了脚步,然后就是一声清脆的声响,壁画亮了一盏灯,那是一盏黄色的小白炽灯,灯光散发着一丝一 丝的昏暗。但也足以让我看清了那个人的面貌了,那是个女人。她穿着一个围裙似的东西,肚子前面顶着一个鼓鼓的包,像是用来装钱的,她的手中握着一柄跟她差 不多高的掸子,另一只手拎着一个板凳。她丝毫没注意到我的存在,而是转身把板凳靠在墙壁边,然后抬起略显臃肿的腿,踩在椅子上,举起担子,踮着脚尖打扫着 天花板上的灰尘,一边掸还一边哼哼着小曲儿。我在旁边看着,并不是注意她是否掸下了什么灰尘,而是打量着她的本人,这是一个中年的女人,个头不高却很壮 实,若是论力气我一定敌不过她,然而我没有感觉到丝毫危险的味道,我虽然没有跟这个女人打过交道,但凭我的直觉,她一定是个好人。
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,她已经注意到了我,我却丝毫没有留意到。
“啊哈——”她发出了一种绵长而又意犹未尽的惊叹声,弄得我一个激灵,我被她吓得有些六神无主。
“小子,你是个猎人么?”
我躲在我的这片黑影里,只是木讷地点了点头。
“你是迷路了?”
“我是不经意找到这儿的。”
“来住店吧!”
“这里是野外的旅馆么?”
“当然是了——”她笑着回应了一下,然后继续忙起了她的事情。她打扫起了稍微低一些的墙壁,也便有力气跟我闲聊了。
“你是走到这里的?那可是很危险的事情啊。”
“不,我有战车,就停在门外。”
“哦,那可真了不起。”这个女人似乎在喃喃自语着。
我此时觉得心安了些,终究不是被她当成了贼,也可以舒一口气了,于是我摸着旁边的一个椅子坐了下来。
坐在椅子上,一种疲意顿时袭来,我脱下手上厚厚的手套,摘下了已经戴了好几天的坦克帽,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。我并没有多想什么,因为我感到我已经没有思 考的力气了,我趴在桌子上,心里只想着睡一会儿。然而就在我有些迷迷糊糊,好像在做梦的时候,我突然听到了那个女人的呼喊。
“小猎人,大门右边的墙壁上有一个开关,你把它打开吧,我该开门了。”我依旧沉浸在梦中,虽然已经睁开了眼睛。我不情愿地抬起头来,瞟了瞟她,看见她正站 在凳子上,她的旁边还有那幅壁画——在微弱的灯光下,那幅壁画的面貌已经显现出来,那是一辆战车,全身上下都是绯红色的,正巧我的眼前十分迷蒙,就感觉那 幅壁画好像是被血染红的,很是瘆人。
“噢。”我发了一会呆,才想起刚才那位女士的请求,迷迷糊糊地回应了一声。然后我走到了门口,摸到了开关。之后吊灯被打开了,很是明亮,可我已是困得不行 了,根本没功夫在这明亮的灯光下看一看周围的装饰,我只注意到旁边有一个更大的桌子和更舒服的椅子,于是就趴在那儿,很快便睡着了。
我大概小睡了两个小时,因为这屋子里非常热,弄得一向因为惧怕寒冷而猫在战车里的我有些不适应。当我把埋在桌子上的脑袋抬起来时,我才发现我已是满头大汗。
我望了望窗外,天亮了,远处的黄沙、矮山和淡蓝色的天空都清晰可见。我走到硕大的落地窗前,抬头望着远方清澈的天空,阳光顺着窗子斜射进屋子,让我感到一丝温暖的感觉,但仅仅是一丝,这时候的太阳刚刚升起不久,看起来现在好像还是上午的时间。
头闷得很,想出去转转,于是我推开了大玻璃门去了外面。我的战车依旧孤零零地停在停车区里,虽然我没带着手套,但我还是我爬上了车头,我想对于我心爱的战 车,我与它没必要讲究太多。摸着冰冷冰冷的铁板,铁板上印着各式各样的瘢痕,比如被蚂蚱加农炮的炮弹打出的凹陷,还有光速蜂鸟留下的痕迹。记得战车手册上 说过,潮湿的季节里,战车装甲的装甲上易长出叫做“铅竹”的东西,据说是一种极其珍贵的真菌,在酒吧可以卖一个很好的价钱。不知道我是否能有那样的好运, 也能在自己的战车上发现一个铅竹,可是现在是冬天,真菌一定不能存活。
今天的风不算大,可以说是自我离开马多以来,唯一见到的没有风的一天,沙子们静静地躺着,只是偶尔刮来一阵风才能将它们卷起来,在低空中划出一条弧线,然 后又顺势落下了。总觉得这样的天很凉,凉得我心里空落落的。自己已经有好几天没看到活人,好几天没张嘴说话了,如果再没人跟我交流我会憋死的,好在夜里的 时候终于遇到了一个人类,我想我现在应该去继续拜访她,就算为自己解闷了。
我走近大门,望着水一般透明的玻璃大门,正巧发现那个女人正站在凳子上,正在挂一个浅绿色的门帘。我只好站在门口,等着她把门帘挂好。后来我有些等不及 了,因为外面虽说没有风,但温度仍旧是非常低的,刚过不久我的手就有一种针扎的感觉,而且我本来就没穿多少衣服,所以身体不停地瑟缩着。于是,我闯了进 去,也没管自己的行为是不是太唐突。
我尽量缩紧身体,趴在桌子上面,一会儿感觉暖和些了,困意再一次袭来。我应该是今天凌晨到的这里,那么现在也不过是刚过去几个小时而已。我整日生活在战车 上,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,生物钟早就乱了,所以现在我只想找一张大床,好好地休息一下。我美美的想着,虽然有想法,可我还是不愿意行动,我宁可像这样在桌 子上多趴一会儿,因为我感觉这样也很舒服。
突然,我感觉有人拍了我的后背一下,我猛然地回头,却发现是那个女人,一脸笑眯眯的模样。
“不要再睡了,你总得订一个房间吧。”
“嗯?”我的脑子还有些不清醒。
“我说,你在这里住,总得先把钱付了。”一提到钱,我的脑子便立即清醒了。
“这里住一天多少钱?”
“这里一共有三种档次的房间——梅、松、竹,竹房一天100G,松房30G,我看你好像个见习的猎人,你还是住梅房吧,一天的房费只有10G。”
“就那样吧!这里有伙食么?”
“当然。”
“伙食很贵么?”
“看你的样子,一天10G足够了。”
“10G?”我不禁喊出了声,因为我的身上总共就带着30G的钱。不过她也很惊奇。
“我这里可不会随意抬价,虽然都是野外的旅馆,但在我这里是这片沙漠里最大的旅馆了,也算有点名气,如果你发现我私抬价格的话可以去猎人办事处举报我。”那个胖女人一脸的信誓旦旦,实在叫我有些招架不住。
“不瞒你说,我只带着30G的钱。”
“哦?难道你不是猎人么?”
“我当然是猎人。”
“你狩猎了么?”
“大概杀了一百多个怪物了。”谈到自己的战绩,我有些沾沾自喜,可是她却打断了我的话。
“那就把ID卡给我吧。”看来她已经听厌了猎人们的吹嘘。可是话又说回来,她嘴里的ID卡究竟是什么东西。
“ID卡?不清楚您说的是什么东西。”
“就是存档机的芯片卡,上面就存储着你所说的战绩。”
“哦,”我想了一下,“存档机上还有这种东西,我怎么没注意过?”
“你还没去猎人办事处领过报酬吧。”
“我正打算回马多去领。”
“在这里也可以,我的旅馆与猎人办事处的线路是相通的,你存档机里所存的赏金也可以在这里取。”
“好吧,我这就去拿。”我格外地关注钱,至少现在是这个样子,一听到自己马上就能花掉自己的报酬,我也来了一种激情,以至于直到上了战车,我才想起我还没有问ID卡具体插在什么地方。看来我也是个钱眼子,我只好回到大厅里向那位女士询问。
ID卡就插在存档机的下面,一个很狭窄的地方。拿到存档机,我用上面的钱订了两天的房间与伙食,我又查询了卡上到底存了多少钱——300余G,听到这个数字我差一点叫出来。
“看来当猎人真是个赚钱的行当。”我想着,默默地走回到桌子旁边,“如果我能杀掉沙鲛,那就能得到1000G的赏金,那可真是一个诱人的数字啊。”不过这些都是幻想,我知道沙鲛是非常可怕的怪物,也许不是我这种见习的猎人能够对付得了得。
那个女人走了过来,把一张纸放在了我的面前,然后她又走到吧台,取出了两个杯子和一瓶酒。
我拾起那张纸,那是这家旅馆的收据,上面印着我的存档机的ID,一些其他的东西,还有一个签名“霞”。
她拿着酒和杯子,坐在了我的对面,斟着酒。
我拿着她给我的那份收据,“霞是您的名字么?”
“是呀,你以后可以直接称呼我霞大姐。”
她倒了一杯酒,推到了我这边,然后她举着自己的那杯酒一饮而尽。我也学着她的样子把酒杯端起来,举到与鼻子平齐的位置。然而刚一闻到刺鼻的酒味儿,我便顿时觉得浑身发麻,而且心里面骤然间生出一种厌恶之情。
“难道是我的年龄还不够?”我想着,我突然有些不想喝酒了,霞大姐并没有劝酒的意思,我端起它来也只是自己好奇,记得凌晨的时候我还好奇过被酒精麻痹的感 觉,可是我毕竟从未沾过酒,我认为像我这么大的孩子并不适合喝酒,而且我也看惯了那群醉酒者的丑态,我可不想变成那样子,于是我放下酒杯,准备打退堂鼓。
我想,那个霞大姐应该不会任由我推开她的美酒,果然,我看她用一幅爽朗的姿态喝了好几杯之后,脸颊上便泛起了红晕,她眯着眼睛一脸甜美的表情,享受了好一会儿。
“你怎么不喝呀!”她伸着手指在空中一边画着圈,一边问我,“多美好的一天,今天我只为你一个人工作……”
她的话让我只感觉犯懵,我再猜她是不是把我当成了她的哪个熟人了,因为我觉得人在喝醉酒的时候一般都会出现幻视或幻听。
“你怎么不喝,这可是我从雨中芭蕾带回来的,正宗的伏特加……霞,话说当年我们还是在酒吧认识的,那次你喝的就是伏特加,可是你怎么喝都喝不醉,不然我也 不会落到你的手里……”她的声音越来越模糊,后来我看她一幅很疲惫的样子,在椅子上有些坐不住了,我刚想起身去扶她一把,她却突然倒在桌子上,睡着了。
“这个霞大姐真是个奇怪的家伙!“我想着,因为她口口声声地说要给我订房间,可现在却睡着了。我拧紧了那瓶酒的盖子,因为我一闻到那瓶酒的味道就觉得浑身不适,而且我也很疲惫了,心里想不如随便找个房间先睡一觉。
我便在走廊里转起来,推遍了所有房间的门,却发现它们全都上着锁。我也试图去叫醒霞大姐,可惜我发现那完全是徒劳的,她除了哼哼了几声,根本没有醒来的意思。没办法,我也只好继续四处闲逛。
走廊里铺着木头地板,跟大厅里的一模一样,虽然陈旧,却很洁净。墙上的内容很新奇,墙上面贴着一种迷彩色的壁纸,类似于一些野战车外壁的颜色,有很重的男 人味。但是有的地方墙皮已经脱落了,有几个很显眼的大窟窿露出黑色的瘢痕,十分的丑陋。我很好奇霞大姐为什么不修补一下这些坑洞,或者直接铺上一层新的壁 纸,这样既有利于外观,又很省事。然而诡异的事情不止这些,墙壁上还挂着一些小画框——都是些战车的艺术画,可我却觉得没什么欣赏价值。之所以这么说,不 是因为画不大方,而是它们挂得太高了,几乎要挨上天棚,根本没办法仔细观摩。这个霞大姐的个头也不算高,她自己也看不到,如果她打扫这些画一定很吃力,为 什么不把它们挂低一些呢?这个霞大姐的思维真是奇怪得很,叫人捉摸不透。
“那些都是我丈夫喜欢的画。”这时候,霞大姐突然清醒过来,“他生前也是一名迷恋战车的猎人。”
“可是,”我说,“为什么要把这些画挂得那么高?”
“因为我并不想看到它们。”
“那就应该把它们收起来。”我若无其事地说着,回到了座位上,然而我马上意识到我刚才说错了话。
霞大姐一直沉默着,用一只手掩着她涨红的脸,过了一会儿,我听到了她微微的呜咽声。
“对不起,刚才……人喝多就容易……乱说话……”她似乎很不舒服,突然站起身来,捂着脸逃进了走廊。
我因为好奇跟了过去,跟着她来到尽头处的一间屋子。我试着推开房门,可我发现里面已经上锁了,我把耳朵贴在门板上,听不到丝毫的声响,我不知道霞大姐究竟 怎么了,究竟在房间里做什么。我有点担心他,看着她半醉半醒的状态,我猜她的心里一定藏着什么事情,也许就像我这样,背负着一段不能与别人分享的经历。
这时我又想起我的事情来,自己已经出来了这么久,究竟是为了什么,我好像从未考虑过这些。我自然想为玛丽亚报仇,可是究竟该去找谁报?酸谷的很多地方都成 了掠夺者的天下,可是我至今还没有正面遇到过掠夺者,据说他们是一些生化人,可他们的外貌、扮相、行为……这些我根本不了解。而且,如果正面遇到他们,我 该怎么办?我永远都忘不了阿梓莎和马多镇所遭遇的灾难,人不可能任凭身边的人死得不明不白的,这些事情像是阴影笼罩在我的心头上。
我只觉得脑子很累,索性靠着墙坐到了地板上。
“这太不现实了!”
我问着自己,自己是如此的弱小,就连一只小小的光速蜂鸟都对付不了,倘若我遭遇了泰德·布罗拉,我恐怕会成为他的烧烤了。可是我不甘心,难道玛丽亚白死 了?作为弱者,我不能挽留她的生命,可是我觉得我至少有能力做些什么,让她的亡灵安息。我要壮大自己的力量,我要让自己变得强大,也许我还需要更强的装备 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。
这时候房门突然间打开了,霞大姐从里面走了出来,她刚看到我坐在地上,连忙扶我站起来,又向我道歉:“对不起,我心情不好,有时候总爱喝些酒,一喝醉又会失态。”
“哦。”我答着,“我什么也没看见。”
“好吧——,你叫什么名字,你好像从来没对我提过。”
“非得说么?”
“天下之大,有很多一面之交的人,交换一下名字也无妨。”
“我叫桑德。”
“桑德?”她很惊异地念出我的名字,“你真的叫桑德么?我记得在十几年前,十字山谷里有一个叫做桑德的孩子,我记得他是玛丽亚的弟弟……”
“不!”我立即否定了她的话,“我来自于马多镇,我是那里的修理工——尼鲁家的远房亲戚。”
我慌乱之中编造了这样一个理由。
“马多镇?”
然而她丝毫没有收起疑惑的口吻,她在盯着我看,我也看着她,她似乎在想着什么。
“你知不知道最近马多发生了一件大事?”
她突然改用疑问的口气对我讲话了。
“不知道。”我故作镇定,“我这些日子一直都在沙漠里狩猎。”
我把头撇向一边,不想被她继续盯着看。倘若此时我的兜里有香烟之类的东西,我会毫不犹豫地点上一支。然而我没有,只得这样傻坐着。
“是这样的啊——”霞大姐的口气忽然间变轻松了,“恕我多嘴,可我一定得告诉你,这的确是一件大事,就在一个月以前,掠夺者袭击了马多镇,据说马多镇被夷为了平地,就连不死女战神都死在了保卫马多的战场上。”
我低着头,此时正在扣着手指头。我正在琢磨回应她的对策,因为我并不想暴露自己与玛丽亚的关系。
“你还没有回马多吧,你应该回去看看你的亲人怎么样了,是不是被掠夺者抓走了。”
霞大姐如是说着。我觉得我终于抓到了一个机会,我呼了一口气,装出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,然后我站了起来,地一脸默然地说:
“给我找间房,我累了,要去休息了。”
我希望我的样子能带给她一种说错话了的错觉,这样她会误以为我真的住在马多镇。这次我低着不语,不再看她,过了一会儿,我听她叹了口气,说“你跟我来吧”,然后她就迈开脚步走了。
我跟在她后面,偷偷地观察着她的行动,她一边走着,臃肿的身体扭来扭去的,走到大厅时,她到柜台后面拿出了一串钥匙,她给了我一把写着门派号的钥匙,告诉 我房间就在左面的走廊。她还说现在店里只有我一位客人,有什么需要尽管提出来,我告诉他我现在只想不被打扰。我不知我的话是不是太无礼了,反正当我接过钥 匙转头离开时,她并没有说任何话。我不知道她的感受如何,对于我而言我感到非常开心,因为我发现我居然还有做戏的天分。
来到客房,我转头就锁上了房门,不禁感叹终于安静了。看着这间“梅”号房,毕竟是最便宜的,所以一切从简,房间也很狭窄,几乎没有装帧,一张灰色的单人 床、一张褐色的小方桌和一把椅子,这里的墙壁只是被石灰简单地刷成了白色,不像走廊那样贴着壁纸,但是墙皮也有脱落,留下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瘢痕。
我脱掉了大衣,以及身上所有沉重的衣物,它们已经陪我度过一个礼拜的时间了,我想它们也该像我一样休息一下了。然后我铺好床,钻进了被子里,感觉就好像回到了尼鲁大爷家。
我仰头望着天棚,又侧着脑袋望了望窗户,那边的窗子很小,而且没有挂窗障,外面的景色一览无余,看着那片毫无生机的荒原,太阳刚刚升起,死气沉沉的荒原忽 然充满了希望似的。而我真的是累了,心想待到太阳落下的时候,这里又会变成死气沉沉的一片,谁知道太阳何时会再一次升起,再一次落下呢——管它是升是落、 是死冬天还是盛夏、是黄昏还是黎明,是有家还是没家……反正我是累了,这些都与我没什么关系。
我想睡觉,我知道做梦的时候可以忘记很多事情。
本文由管理员发布于:2018年01月15日